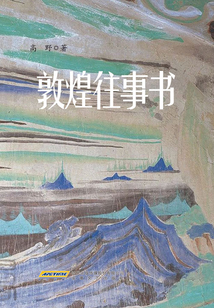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盂蘭盆節
盂蘭盆節那一天,敦煌上空懸起了幾朵鴉青色的云。
天剛蒙蒙亮,昨夜的雨喂飽了大泉河,讓它變得如同白羊羔一樣光潔溫馴,不停絮絮低語。這時,自作多情的人們往往就會想,雨云正是為了打擾人們今晚放河燈而飄來的。年輕畫師明月奴一夜聽著河流漲水的聲音,還以為是李三郎趁著他睡得迷迷糊糊的時候,在胡亂地翻他先前理好的畫稿。在睡夢中他已計劃好,一醒過來就跟李三郎理論,正如他在睡夢中已計劃好如何在最近興建的小佛窟東壁畫些什么一樣。可當他真的揉著眼睛醒來,看見李三郎非但沒有翻他的東西,甚至還沒有醒,氣就全消了,反倒親熱地搖起熟睡中的李三郎的肩膀:
“三哥,三哥,咱們走吧,五更天都過啦!”
因為節日的緣故,兩個小伙子得了幾天空閑,準備騎上馬,往沙州城的集市里去,盤算著晚上再回到千佛洞這里看河燈。
他們出門時,下面那一個住人的窟里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音。看到明月奴的身影在階梯上晃動,那窟里探出一個燕子般黑黑的腦袋。明月奴心里清楚這人在說什么,就故意把腳往木頭階梯上狠狠一磕,梯子下的崖壁撲簌簌向下落土,落了那人一頭一臉,嗆得他不停咳嗽。
畫師們常議論,楊武齡師父那樣和善,怎么把大徒弟教成了這個德行。最為平常的一種說法是,正是楊老頭太過好脾氣,從不給徒弟吃板子,才把他慣得好比出籠的長毛獅子一樣跋扈,比沒穿鼻繩的駱駝還驕橫。他們一邊說著,一邊琢磨如何用新鮮柳條去抽學徒的手心。
還有一種說法更惡毒些,不過也的確觸到了更為黑暗幽微的生命之源:明月奴是個雜種。雜種就是那些頭系輕絲發帶、腰懸羊脂美玉的貴族老爺在他們文縐縐的語言里稱為“庶子”的不速之客,那種常常被膽戰心驚的姑娘們扔到疏勒河的蘆荻叢里自生自滅、誰也不歡迎的東西。
可是,在這個天空低矮湛藍好似佛窟穹頂、房屋單薄潔白如同供桌上的琉璃寶塔的地方,常常是雜種出好漢,也許明月奴只是盡了一個雜種的本分而已。更為過分的是,他竟還是胡女的兒子。而胡人,胡人能是怎樣的呢?胡人多是兇惡、野蠻,連小手指都散發著狗一般的膻味,經常在酒肆里喝得爛醉又賴賬不還的貨色。明月奴雖然從沒喝醉過,但是他的確愛逛小酒館。踏歌、斗雞、飛盧擊鞠,他都非常愛玩,也都是好手。
“瞧著吧!”剛被落了一臉灰土的泥塑匠董興憤憤然,“他一準會闖出禍來!就是這樣。”他抖了抖肩膀,灑落一地灰土,“這狗崽子遲早會被抓到班房里去。”
“你們還記得請楊畫師為新窟作維摩詰經變畫的供養人嗎?”董興朝身邊的人說道。
幾位畫師都還記得那家人,他們是本地望族曹氏的支系,家里有兩位女公子:大些的那個相貌平平;小的那位名叫襄娘,十五六歲,畫著短短的蛾眉,眉心一點朱紅的花鈿,美艷里卻透出幾分戾氣。據說這家父親正是為了她來建窟祈福的,姑娘生來就得了一種怪病,經常陷于睡夢中,時常要用細針將十指都扎出血才能蘇醒,有時明明眼睛睜著,卻始終喚不醒,家人只能看著她在庭院里一圈一圈地徘徊。
“當時畫維摩詰的正是明月奴,而且你猜怎么著?他把維摩詰大士畫得和自己有八分像,這襄娘看了心生愛慕,當晚趁著父母和姐姐睡著,就跑去跟他相會。”
畫師們半信半疑。
“怎么,你們還不相信?我當天回來得晚,在拴馬的時候就看到后山有兩個人影,一個梳著發髻,大概是那姑娘,另一個,大概就是明月奴那乞索兒。”
聽者們紛紛起身,不愿再聽這老套故事,直到董興說道,事實遠比故事可怕。出于某種不為人知的原因,那位姑娘在這次佛窟之行后,病情非但沒有好轉,反而加重,回到沙州城就去世了。
“你們以為,曹家建的佛窟里,新開的一個小窟是為了什么?那是為了死去的襄娘往生。我要是這家父親,是絕不會把佛窟還交給明月奴來畫的,你們看他那樣得意,指不定是在發死人財。”
天色很明凈,好像對過白蛤粉的靛青色,風卻陰冷陰冷的,好像是從見不到太陽的地底刮來的一般。這盂蘭盆節的到來,不僅模糊了陰陽兩界的界線,也讓老畫師們的思緒陡然開闊:那登徒子明月奴的生辰難道不正是七月半嗎?他性格這樣傲慢,還克死了別人的女公子,肯定是惡鬼轉世,也不知道是哪年盂蘭盆布施的時候,扒著河燈來到人世的。老畫師們面面相覷,一片唏噓,心里暗暗覺得既恐怖又有些失落,無論是謠傳也好,真事也罷,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那就是從未有人和他一樣,能在漆了一半的金剛力士那黃澄澄的金剛怒目下,掀開供養人千金的裙子。
是惡鬼或不是,誰也說不清。小伙子們早已走上去沙州城的大路,清早,路上人不是很多,兩匹馬駒緩緩地走著,兩個騎手各有心事,思緒生長出來,籠罩他們,如同道路盡頭升起的濕潤的霧靄。
李冉枝是宗室子,是高宗皇帝之孫汝陽王的曾孫,他和他已經去世的父親,除了宗室名號一無所有,卻始終不見他去應舉為仕,反而時常往楊武齡師父這里跑,跟他學畫,他幾乎是和明月奴一起長大的。可是冉枝騎馬時有一種高貴的氣度,談吐間也有一種讓人愛慕卻畏懼的氣息,以至于見過他的總角小兒和少年郎,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叫他“三哥兒”,不能喊他一起去捉蚱蜢、騎竹馬、糊風箏了。
而明月奴的心事則永遠同他新接的壁畫有關,世間其他的一切,他只有模糊的印象,并沒有什么興趣。他實在靈巧:一雙神情淡漠,但是在勾勒墨線時分外明亮的灰藍色的眼睛;兩道烏黑的、女子似的彎彎眉毛;同樣烏黑的頭發是從來不束起來的,而是像喜鵲的兩只翅膀一樣短短地垂在小氈帽底下;最為靈巧的是那雙手,他自己心里明白,那些中年畫師譏刺嘲諷,各式編派他,不過是妒由心生。這些所謂大師多半已經江郎才盡,只能模仿前朝人的畫風,筆法干裂粗糙,此外還擅長給徒弟吃板子。而明月奴卻擅長一切,羊毫畫筆似乎是他伸展出的軀體。似乎他活在一個更為靈動的人間,那里風是慢的,山會生長,石頭在河水里快速走動,萬物從出生到衰弱、死亡、腐爛,似乎極度漫長,又極為短暫。
他將為曹氏襄娘的往生祈福窟畫孔雀明王。
“我再也沒法教你什么了。”師父笑著,“西魏大師們估計都畫不出來你這樣的卷草紋和云紋。可是,我總覺得,你的畫里好像還是少了些什么,它們沒能活過來。”
他只十七歲,但人們可以預見,如果他沒有從腳手架上摔下來變成殘廢,沒有因濫賭而被放債人砍去手腳,也沒有被永遠不會攻進沙州城的吐蕃人捉去做苦力的話,待到他二十五歲的時候,他一定會長成一個高大漂亮的青年人。如果再留上一撇唇髭,戴尖頂花瓣冠帽,著紺青輕羅衫,絕對會酷似那些前朝大師所塑的男菩薩。自從樂遵和尚頭一個開窟造像以來,多少畫師、工匠都是頂著同一副瘦小枯黃的面孔,言語少過還沒來得及添上嘴唇的泥塑像,而明月奴卻可以算是一個生機勃勃、放蕩不羈的例外。少年人那種混雜著純潔、傲慢、兇暴和嫉妒的血液正夜以繼日地在他身體里奔流,絲毫沒有停息的征兆。
大路旁的荒地上晃動著幾個人影,明月奴瞇起眼瞧起來,朝著他們招了招手。果不其然,荒地那邊一個人站起身來,接著傳來一聲綿長的呼哨。
“那是誰?”
“名字嘛,好像是符也門延那。”明月奴小聲說出一串奇特的音節,這語言聽起來好像是一串錢幣互相摩擦,又像是陶匠的刮刀在泥坯上輕柔地劃過。
“我不懂粟特話,他的漢名是什么?”李冉枝問。
“嘿,我其實也不懂,他是安國人,大家叫他安延那。但是他自己不喜歡別人這么叫他,非說他的名字本義是‘神愛’,偏讓人叫他神愛。和他一起的那幾個,大概也是行腳商吧。但是我看他們現在是在刨墳,去年秋分的時候他領著我也去了。從這里往東去兩里地,老墳里好東西可多了。”
“當真?”李冉枝擰起眉頭。
“那還有假?”明月奴笑起來。
“你怎么認識這種人,干起這種勾當?”
李冉枝揚起馬鞭,不由分說地抽到明月奴的棉袍上,朝著他的肩膀后背一通好揍。
“哎呀!挖的又不是你家皇帝祖墳,你打我做什么?!”明月奴慌忙策馬向前,而冉枝卻不依不饒地追過去,不一會兒他們就沒影了。
從千佛洞到沙州城的二十里路的路邊,連綿不絕地散落著一些烽燧和古墳。
安國商人神愛時常會在這里碰碰運氣。神愛二十歲——多數安國粟特人十六歲出門做生意碰運氣——經商四年就能穿起藍底繡金絲的毛織外袍,擁有一支駝隊、兩個商鋪和三個溫順的綠眼女奴。這并不是因為他兢兢業業,實誠交易,正相反,神愛確實是沙州人土話里叫作“市郭兒”的投機商。他不信佛祖也不信他們粟特人的祆神,對于賤買貴賣根本毫無愧意,他根本不介意對著沙州府的小吏點頭哈腰以求得一張附籍少稅的文書,他賭博、斗毆、嫖妓,常常鼻青臉腫地在骯臟的巷子里醒來。當然他也不會介意從這些古代的墳堆里搜尋金步搖、發簪、祖母綠扳指、有些發黑的銀質衣帶扣,然后在黑市上賣出高價。他似乎是完全出于自愿,而且頗為自豪地要過一種恬不知恥的生活。被神愛光顧過的墳塋里,有許多一千年之前的人在安眠,他只要瞧一眼這些人最后的衣著,就能知道他們曾經有過怎樣的生活,能知道如果他敲開他們的牙齒,會發現一枚爛銅錢還是一塊小小的玉石。還有一些墳墓過于古老,見多識廣如神愛,都無法辨識出年代。因為氣候干燥,有些死者還面目如生地靜靜躺在雞鳴枕上,頭戴裝飾著黛綠羽飾的帽子,仿佛只是在下午小睡。每當看到這種景象,神愛都會產生對死亡的千百種困惑,然后又下定決心要把自己恬不知恥的生活一天天或愉快或痛苦地繼續下去。
而今天安延那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收獲,只是在快要崩塌的一座古代烽燧里刨出了一個半朽的大木頭匣子,匣子上的鎖已經銹成了一團。他拿起一塊石頭砸了四五下,爛鎖掉了下來,匣子里是一堆銹鐵和幾張鞣制過的甚至還有些柔軟的羊皮。安延那招呼了同來撈偏財的幾個雇工,一齊觀察起那匣子上奇特的、彎彎曲曲的文字。沒人能認出來這是什么。那些符號散落在紙上,每一個都好像一座小小的城池,好看卻無用。神愛剛想把它丟棄,卻發現這些羊皮底下竟還有一沓寫著漢字的紙張,他抽出一張,紙已變得薄而脆,依稀辨認出來,卻像是一首小曲兒: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臨池柳,這人折去那人攀,恩愛一時間。”
似乎還是出自一百年前,也許兩百年前一名極卑微的煙花女子之手。
神愛抖了抖那老舊的紙張,嗤笑一聲,盤算起怎么把這東西賣給沙州城里那些士大夫和學士郎。他想著,當那些出身高貴、纖瘦白皙的郎君讀著這些曲子詞,為死人暗暗嘆息落淚的時候,他也許可以拿著賣這些古董的錢,到某個還活著、心跳有力的女人那里買到一個美妙夜晚。
想到這,他自己都不由得佩服自己經商的天賦。
敦煌,或者按照他們那時的稱呼,沙州,在節日盛會時聚集了十里八鄉所有的色彩、聲音和氣味。而在一切事物當中,年輕姑娘們的裙裝是最為艷麗的。襦裙和間色裙拂過地面,地上仿佛落下一層層花瓣,又好像豎起一把把匕首。于是許多壞念頭開始從角落里升起來,許多好念頭也浮現,婚禮、情殺、械斗,立刻近在咫尺。
人的眼睛也色彩紛呈、形狀各異,它們有的發藍綠色,有的深而黑,有的金褐色好像蜂蜜,有的眼睛細長如縫,有的好像杏仁,有的圓如銅鈴,所有的眼睛都是美的,但是不知道為什么長在多數人臉上看起來都奇丑無比,大概是由于多數人都面目庸俗,而且像老駱駝一樣缺著牙齒。
色彩稍少些的是牛羊鋪子,有些鋪子上用鐵鉤子掛著剛剝下皮的羊羔,血肉模糊的蹄子還一動一動的,大的鋪面前多半是有一汪汪新鮮的水紅、玫紅或鮮紅的血液浮在木板上。而小的鋪子上紅色是很少的,往往都是黑壓壓一片蒼蠅繞在一片片青黑的、已經風干的肉上,瘦骨嶙峋的鋪主和衣衫襤褸的買家互相瞪著眼,討價還價,活像兩只禿鷲。
人人都高聲說話,城內喧嚷至極,就像羊角風嗚嗚地席卷了一切。還有來往行人的體味,木匠身上有木頭味,鐵匠身上有鐵味,胡餅坊主有胡餅味。有些士族子弟騎著高頭大馬,衣袖上飄來竹葉和露水的清香,但是這種香氣轉瞬之間便和來往行人的汗臭、燒烤熟食的煙味以及羊和駱駝的臊氣混在一起,顯得氣味更加怪異。這是中午時分,好不炎熱,這些色彩、聲音和氣味一齊在太陽底下蒸騰起來,摩肩接踵的行人們容易產生自己是在海市蜃樓的街道上行進的錯覺。這并不是什么好事,因為數年之前,也是盂蘭盆會,不知是誰踩錯了步子壓到別人身上,使得人群像發瘋的馬群般亂了陣腳,生生把十來個倒霉鬼的臉踩得稀爛,連親爹見了都認不出了。
那時盛唐的余暉還沒有退去,從高門大戶到市井小民,都對音樂、舞蹈、詩歌和故事十分著迷。如果在茶館或者酒肆小坐,十有八九會碰見音聲人和講唱人賣藝。安延那就在這樣一家小酒肆的臨窗的位置上坐下了,大方地把三枚銀幣拍在桌子上,點了一碟梧桐餅、一碗蒸羊肉和一碟瓜果。不遠的一張桌邊,兩個講唱人手執繪本應景地唱著盂蘭盆節的老典故——目連和尚地獄救母的故事。
安延那雖然漢文很好,聽起故事綽綽有余,可是當那講唱人一唱起韻文,他就昏天黑地聽不明白,只能跟著其他聽眾一起叫好。
鐵輪往往從空入,猛火時時腳下燒。
心腹到處皆零落,骨肉尋時似爛焦。
“好!好!好!”安延那拍起手來,他最喜歡這等地獄景象的唱詞。
幾個百戲子踩著高蹺,從街道上方悄悄掠過,輕捷得如同燕子剪刀似的尾巴。人群聚攏來,中心空出一個圓圈,五個粟特胡人演起幻術:他們吃火,然后吐出來,就像夜里戈壁灘上的蜥蜴和蛇。只不過蜥蜴吐的是黃綠色的火,蛇吐白火,而這些幻術師食火時火是通紅的,吐火時噴出的卻是藍焰。
等到火焰熄滅,七圣刀就開演了。一個紅發大漢拿起彎刀在腹上切開一個口子,挖出心肺,若無其事地把腸子扯出來,就像扯麻繩,于是歡呼聲四起。有七歲小兒騎在父親脖子上,和他大聲爭論幻術師的胸骨是青白色還是黑色。另一個歪嘴胡人捧起大鈴鼓,賞錢從人群里飛出,砸在鼓面上,鈴鐺齊響,悅耳動聽。
這時神愛看到一個清瘦敏捷的少年繞到了那紅發漢子的身后,悄悄把手伸進了他的衣服,然后——從那紅發大漢的衣兜里掏出了先前幻術里的心、肺和腸子。這時候那些癡癡地望著的人們才發現:不對勁,這不是羊的心、肺和腸子嗎?
看表演的人群爆發出噓聲。
那些玩七圣刀的粟特胡人不滿意了。為首的彪形大漢大為光火,一拳砸在那小阿郎眼眶上,阿郎閃避不及,還來不及出聲就被打倒,幾個黃胡子紛紛圍上去,不由分說又是拳腳相加。圍觀的人見到這場景,先是小心翼翼地后退了幾步,接著又饒有興味地聚攏了回去,確切地說,是更加饒有興味地聚攏了回去。
神愛攔住鄰桌:“那邊怎么回事?怎的下手這么狠?莫不是要把眼睛打瞎了?”
“瞎了又怎樣?那阿郎自作自受,拆人場子,斷別人財路……”
神愛輕笑一聲,剛準備湊過去看,耳邊就傳來那個阿郎破口大罵的聲音:“你娘老子的打我眼睛!”
是個熟悉的聲音。
他定睛一望:“娘老子的!那是明月奴啊!”
他傾身朝窗外探去。
大事不好。
安延那沖出酒肆,擠開人群,朝那領頭的嚷嚷了一通粟特話,紅發大漢才松開明月奴的衣領。
安延那低頭一看,這還了得?血流了一頭一臉,而且只見出氣不見進氣了。
李冉枝牽著馬從岔路口走過來,和衣襟上滿是血的安延那撞了個滿懷。
“明月奴被人打了。”安延那說。
“足下是……”
“莫管我是誰,你瞧瞧他就知道了。”
冉枝半信半疑:“我還沒走多久,就被打了?”
“被人打了眼睛,會瞎的,你快把他帶走!”安延那比畫著。
“什么?”
等到飛奔過去,望見那個人被打得就像被馬群踩過似的,李三郎就覺得自己成了一塊燒紅的鐵,一瞬間被人扔進了水里。打瞎了。瞎子。看不見。瞎子。李三郎心里一沉,他還沒來得及好好揣摩這詞的確切意思,心里就隱隱覺得明月奴并不會瞎,而是會死。
真是盂蘭盆節不出門,出門就撞鬼。
兩個人把不省人事的明月奴架到李冉枝的那匹青馬駒上,用一條腰帶把他和馬鞍捆在一起。明月奴的血滴落在地上,一滴,兩滴,三滴……野狗尾隨他們走了好一會兒,把血舔得干干凈凈。從酒肆到最近的醫館,往南走一共四條街,每條街的狗聞到人血味都一齊吠了起來。
“呸!這哪里是狗,簡直是狼!”
醫師看了看小阿郎的眼睛,搖了搖頭:“這只眼睛廢了。要是發起熱來,另一只也不知能不能保住。”這老郎中看起來有九十歲了,這讓他的話可信度提高了三分,并不是因為醫術多么高超,而是這么一把年紀,怎么著也和病、死至少會過幾次面。他仔細包扎了少年的左眼,抓了些草藥,就讓冉枝和神愛離開了。
天徹底暗下來的時候,他們離千佛洞已經不遠,明月奴從昏迷中醒來,感到眼眶里的劇痛,不由得急促地吸氣。冉枝伸手撫上他的額頭:反常地熱。
“明月兒,你還能看見什么?能看見就說出來,讓三哥知道你還能看見。”
“我右眼還能看見,不清楚,可是我看見大泉河了……我們什么時候過河?”
“快了,就快了,過了河,到了家里喝了藥躺一陣,你就會好的。”冉枝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跟你說我看到的啊,我看見沙州城在后面,城墻離得這么遠都能看見,那些亮光,是城里面有人出來夜游了吧……千佛洞里也有燈……我還能看到……師父大概也在點燈了……我看見大泉河上在放河燈了,好像一條河都被點著了。三哥,你瞧瞧,都有些什么燈啊,那么多顏色,好多人出來放河燈了!”
明月奴很是惶恐,一個接一個地點數著他能看見的東西。
“有蓮花燈、船燈,還有金魚燈……”
然后那條光之河卻漸漸暗淡了。
明月奴趴在馬背上,奮力地眨著眼睛,可是無濟于事。眼前一片黑暗。
“三哥,三哥!那些河燈是都沉下去了嗎?”他慌張地叫了起來,“沉下去了嗎?!還是我看不見啦?”
盂蘭盆節從天上和地底下盛大地降臨人間,它到來的聲音震耳欲聾,好像最炎熱的正午,空無一人的街邊,瘸了一條腿的老乞丐,支起那條柳木拐棍敲在地上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