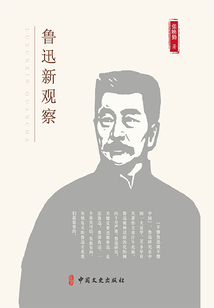
魯迅新觀察
最新章節(jié)
書(shū)友吧第1章 魯迅兄弟反目探微
多年來(lái),魯迅“兄弟失和”的話題一直是魯研界的一大疑案,兩個(gè)志同道合、感情深厚的親兄弟為什么會(huì)突然間分道揚(yáng)鑣、手足情斷??jī)蓚€(gè)當(dāng)事人——魯迅(周樹(shù)人)和周作人始終回避這個(gè)話題,相關(guān)人士對(duì)此諱莫如深、守口如瓶,更增加了事件的神秘性。我看過(guò)不少相關(guān)的材料和分析文章,但都各執(zhí)一端,很難讓人信服。有些人出于維護(hù)魯迅的立場(chǎng),談到關(guān)鍵問(wèn)題時(shí)總是閃爍其詞,為尊者諱;有些人則對(duì)此津津樂(lè)道,憑空想象,捏造虛構(gòu),對(duì)魯迅進(jìn)行攻擊栽贓。
實(shí)事求是地講,“兄弟失和”這個(gè)問(wèn)題,屬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私密話題,當(dāng)事人雙方不站出來(lái)說(shuō)話,旁人是不可能說(shuō)清楚的。但是我們可以通過(guò)史料分析、當(dāng)事人的回憶,力圖接近事實(shí),破譯事件背后的一些東西。
1.平靜中潛藏著危機(jī)
魯迅和兄弟周作人絕交的發(fā)生地是在他們居住的北京西城區(qū)西直門(mén)內(nèi)公用庫(kù)八道灣胡同十一號(hào),那我們就先從八道灣說(shuō)起。魯迅是一九一二年五月隨中華民國(guó)臨時(shí)政府教育部從南京遷到北京工作,周作人是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北京大學(xué)任教,兄弟二人當(dāng)時(shí)在北京沒(méi)有買(mǎi)房子,寄居在紹興會(huì)館的補(bǔ)樹(shù)書(shū)屋,家屬都在紹興老家。一九一九年,兩個(gè)人工作穩(wěn)定,收入頗豐,而老家紹興新臺(tái)門(mén)的周氏舊宅又要賣(mài)出,這一年年底必須搬離,于是他們產(chǎn)生了在北京買(mǎi)房、接全家人定居北京的打算。
在買(mǎi)房子的問(wèn)題上,魯迅和周作人最初的想法不完全一致。作為兄長(zhǎng),魯迅是希望將紹興老家聚族而居的方式移植到北京,兄弟三人(另有三弟周建人)一家和老母親一同生活,和睦相處,其樂(lè)融融。周作人受日本太太羽太信子的影響,希望能獨(dú)立門(mén)戶(hù),單獨(dú)生活。當(dāng)然,最后他們還是尊重了大哥魯迅的意見(jiàn),全家合買(mǎi)一處宅院,過(guò)著紹興臺(tái)門(mén)里的大家庭生活。
當(dāng)時(shí)北京的房子以四合院為主,大小不一,星羅棋布。為此魯迅費(fèi)盡了周折,最終買(mǎi)下了一處大房子,這就是北京西直門(mén)內(nèi)公用庫(kù)八道灣胡同十一號(hào)院。
魯迅在日記中記載:“擬買(mǎi)八道灣羅姓屋”(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買(mǎi)羅氏屋成”(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經(jīng)過(guò)裝修后,十一月二十一日魯迅和周作人一家“移入八道灣宅”。十二月二十九日魯迅從老家紹興接母親、妻子和三弟周建人全家赴京入住其中。
八道灣胡同十一號(hào)院原來(lái)是羅姓的一處坐北朝南的大宅院,院子分為前、中、后三進(jìn),外加一個(gè)西跨院。空地較多,便于孩子活動(dòng)。魯迅購(gòu)房后,對(duì)房屋進(jìn)行了必要的修繕。
當(dāng)時(shí)居住的情況是:魯迅的書(shū)房和臥室開(kāi)始先在中院西廂房三間,后來(lái)改住前院前罩房中間的一套三間房子,以便于靜心寫(xiě)作;魯迅的母親魯瑞和妻子朱安住在第二進(jìn)中院正房的東、西兩間;后院第三進(jìn)的房子最好,周作人一家住后院北房的西側(cè)三間;周建人一家住后院中間的三間;東側(cè)三間是客房,他們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羽太芳子名為妯娌,實(shí)為姐妹,生活方式生活習(xí)慣比較接近。
當(dāng)時(shí)魯迅在教育部當(dāng)科長(zhǎng),月收入三百大洋,周作人在北京大學(xué)當(dāng)教授,月收入二百四十大洋,周建人暫時(shí)沒(méi)有收入,先在北京大學(xué)旁聽(tīng),后于一九二一年九月只身到上海商務(wù)印書(shū)館當(dāng)編輯,留下妻子兒女在八道灣生活。
魯迅和妻子朱安感情不和,長(zhǎng)年異地生活,偶在一起也處于分居狀態(tài),到北京后仍然未與妻子同居。魯瑞喜歡朱安做的家鄉(xiāng)菜,兩個(gè)人生活習(xí)性相近,在中院吃飯,朱安負(fù)責(zé)照顧婆婆的日常起居。魯迅后來(lái)則干脆入伙后院,與周作人一家同吃日本餐。
八道灣里兄弟三家和睦相處,有錢(qián)大家花,有飯大家吃,表面上風(fēng)平浪靜,兄弟怡情,一片祥和,暗地里卻潛伏著危機(jī),這種聚族而居的平靜生活維持了三年多時(shí)間。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表面上和睦的家庭終于出現(xiàn)了終身無(wú)法彌補(bǔ)的裂痕。魯迅與周作人關(guān)系破裂,反目成仇。魯迅在這一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記中記下了如下一筆:
十四日 晴。午后得三弟信。作大學(xué)文藝季刊稿一篇成。晚伏園來(lái)即去。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
三弟即周建人,當(dāng)時(shí)只身在上海商務(wù)印書(shū)館當(dāng)編輯,魯迅看信寫(xiě)稿會(huì)朋友,看似很平常。但重點(diǎn)在最后一筆:從這一天晚上開(kāi)始改在自己的屋里吃飯。為什么平時(shí)好好地和二弟一家在一起吃飯,卻改成了自己吃了呢?而飯菜很可能不再由后院提供,而是夫人朱安做的。
這一天到底發(fā)生了什么?魯迅雖然沒(méi)有做詳細(xì)的記錄,但卻寫(xiě)了一筆“此可記也”,說(shuō)明心里相當(dāng)在乎這件事。周作人在這一天的日記中沒(méi)有提及此事,此中必有難與人言的隱情。
我們知道,魯迅不僅不是白吃飯,而且是交了大筆錢(qián)的,他的工資當(dāng)時(shí)比周作人要高,大洋三百,周作人是大洋二百四十塊,魯迅還有稿費(fèi)、講課費(fèi)的收入,即使不是全部拿出來(lái)養(yǎng)家,以他一貫的做法,交家里的生活費(fèi)一定占有相當(dāng)可觀的比例。周作人不僅比他掙得要少,而且家累負(fù)擔(dān)也重,還有三個(gè)孩子,而這時(shí)周家主持家政財(cái)政大權(quán)的既不是魯迅的母親魯瑞,也不是魯迅的妻子朱安,而是弟妹——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按常理說(shuō),像魯迅這樣一位財(cái)神爺,請(qǐng)都請(qǐng)不來(lái),哪有往外趕的道理?所以問(wèn)題不應(yīng)該出在經(jīng)濟(jì)上,而是在其他方面。這種突然的變化,不知他對(duì)母親魯瑞、妻子朱安如何解釋。
這一年魯迅四十二歲,周作人三十八歲,羽太信子三十五歲。
此后的五天,我特意查過(guò)當(dāng)年的氣象記錄,七月中下旬的北京一直在下雨,魯迅在這幾天的日記中寫(xiě)的文字簡(jiǎn)略,但都記下了氣候變化。天氣悶熱,又陰雨連連,加上家里突然發(fā)生的這種變化,八道灣十一號(hào)周宅的家庭氣氛肯定是緊張壓抑得讓人喘不過(guò)氣來(lái),這一切肯定讓魯迅心煩意亂,坐立不安。
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八道灣從七月十四日那天起潛藏著一種危機(jī),兄弟倆突然不在一個(gè)桌子上吃飯了。這之前,沒(méi)有任何征兆,兩個(gè)人的關(guān)系較一般的兄弟更為密切:相同的家庭、相同的成長(zhǎng)經(jīng)歷、相同的教育背景、相同的志趣愛(ài)好、相同的社交圈子,兩個(gè)人在日本和北京時(shí)期曾同屋而居很長(zhǎng)時(shí)間。就在事發(fā)前的一九二三年上半年,兄弟倆還經(jīng)常在一起,宴請(qǐng)朋友、出席聚會(huì)、帶孩子逛公園、“小治肴酒共飯”等等,十天以前的七月三日,兩個(gè)人還同去東安市場(chǎng)、東交民巷書(shū)店、山本照相館等處逛街購(gòu)書(shū),這些,在魯迅的日記中都有記載。兄弟之間沒(méi)有任何產(chǎn)生矛盾相互疏遠(yuǎn)的跡象。十四日這一天是轉(zhuǎn)折點(diǎn)、導(dǎo)火索,引爆了他們之間潛在的矛盾。
2.一封意想不到的絕交信
果然在五天以后的七月十九日上午,周作人親自到魯迅屋里送來(lái)一封自己寫(xiě)的信,外面寫(xiě)著“魯迅先生”,信的內(nèi)容如下:
魯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過(guò)去的事不必再說(shuō)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dān)受得起,也不想責(zé)誰(shuí)——大家都在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色的夢(mèng)原來(lái)卻是虛幻,現(xiàn)在所見(jiàn)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請(qǐng)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lái)。沒(méi)有別的話。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的這封信,是他自己在十九日上午拿到魯迅房間的。魯迅看了信后,“邀欲問(wèn)之”,周作人沒(méi)有理會(huì),魯迅也沒(méi)有再去溝通。
收到這封絕交書(shū),魯迅在當(dāng)天七月十九日的日記中記下一筆:“上午啟孟自持信來(lái),后邀欲問(wèn)之,不至。”啟孟即周作人。
下面我們來(lái)逐句分析這封信背后透露的一些信息:
“我昨天才知道——但過(guò)去的事不必再說(shuō)了。”
這說(shuō)明周作人是突然知道的,是有人告訴他的,這個(gè)人應(yīng)該就是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至少?gòu)钠咴率娜詹蛔岕斞冈诤笤撼燥埬翘炱穑鹛抛颖汩_(kāi)始逐步向周作人透露了一些事情,直到昨天——十八日才斷斷續(xù)續(xù)地說(shuō)清楚。大哥好好地在后院入伙吃飯,突然不讓人家來(lái)了,羽太信子必須要給丈夫一個(gè)交代,找一個(gè)合適的理由。至于她說(shuō)了什么?過(guò)去發(fā)生了什么事?周作人沒(méi)有明說(shuō),但肯定自以為是有辱于他、讓他難以忍受、難以啟齒的所謂大哥對(duì)妻子有“失敬”之事。
“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dān)受得起……”
基督徒以仁愛(ài)、慈善、忍耐、平和著稱(chēng),上帝說(shuō):“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duì)。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zhuǎn)過(guò)來(lái)由他打。”周作人這句話的意思無(wú)非是說(shuō),如果我不能擔(dān)受不能忍受,后果將不堪設(shè)想,至少事態(tài)不會(huì)像寫(xiě)一封絕交書(shū)這樣簡(jiǎn)單,說(shuō)明他認(rèn)為知道的事情性質(zhì)是非常嚴(yán)重的。
“我以前的薔薇色的夢(mèng)原來(lái)卻是虛幻,現(xiàn)在所見(jiàn)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薔薇色的夢(mèng)”,就是夢(mèng)想三兄弟住在一起和睦相處,永不分家,重現(xiàn)老家聚族而居其樂(lè)融融的景況,現(xiàn)在無(wú)情的現(xiàn)實(shí)擺在那,理想破滅了,夢(mèng)想是虛幻的,而現(xiàn)實(shí)殘酷無(wú)情。到底發(fā)生什么事,周作人只字未提。
“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意思是說(shuō)看破了虛幻的偽裝的現(xiàn)實(shí),周作人決意改變自己以往理想化的想法、態(tài)度,與大哥決裂,換一種活法,走自己的路。
“以后請(qǐng)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lái)。沒(méi)有別的話。愿你安心、自重。”
這是周作人與大哥魯迅絕交,下逐客令,不讓魯迅以后再到自己房里,甚至不屑再說(shuō)什么。最后又用了“安心、自重”四個(gè)字,大哥魯迅有什么對(duì)不起他的,有什么不安心的、有什么不自重的行為非要讓你當(dāng)?shù)艿艿闹附棠兀匡@然周作人的話里有話,氣憤已極。
魯迅接到這封信肯定有如三九天冷水潑頭,渾身發(fā)冷,這種語(yǔ)氣、這種措辭簡(jiǎn)直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他沒(méi)有做出任何激烈的反應(yīng),而是默默地忍受了。他本想找二弟解釋一番,“邀欲問(wèn)之,不至”,很可能讓傭人到后院找過(guò)周作人,但對(duì)方不來(lái),他也不能去,只好不再堅(jiān)持。
周作人的這封信話里有話,語(yǔ)氣冷硬,按理說(shuō)魯迅受到誤解,你不來(lái)我也要找上門(mén)去說(shuō)清楚,至少應(yīng)該寫(xiě)一封信為自己辯解清白,自己不去送也可以派傭人送去,但是他沒(méi)有這樣做。
以魯迅的性格,疾惡如仇,錙銖必較,與對(duì)手論戰(zhàn)決不手軟,聲稱(chēng)對(duì)敵人“一個(gè)也不寬恕”,豈是輕易會(huì)讓人誤解污蔑的,這一次卻破天荒地忍下來(lái)。兄弟無(wú)情,發(fā)難在先,他不會(huì)光是為了顧及情面,就作沉默狀吧?!很可能事情嚴(yán)重到了難以解釋的地步。
我們?cè)賮?lái)看看這一天周作人是怎樣記錄此事的。
查《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七日:
陰,上午池上來(lái)診。下午寄喬風(fēng)函件,焦菊隱、王懋廷二君函。七月小說(shuō)月報(bào)收到。得玄同函。
記到此處戛然而止,在與“十八日”日記之間,空了一行,周作人在這里動(dòng)了剪刀,剪了大約十個(gè)字。在這么重要的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上,在給大哥絕交信的當(dāng)天,他的日記破天荒地突然剪掉了一處,而且是唯一的一處,是什么不為人知的內(nèi)容呢?
直到二十世紀(jì)六十年代,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錄》《一四一不辯解說(shuō)(下)》中才就此事做了簡(jiǎn)要說(shuō)明:
關(guān)于那個(gè)事件,我一向沒(méi)有公開(kāi)的說(shuō)過(guò),過(guò)去如此,將來(lái)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記上七月十七日項(xiàng)下,有剪刀剪去了原來(lái)所寫(xiě)的字,大約有十個(gè)左右。
這一天的日記,周作人肯定記下了與魯迅失和事件有關(guān)的文字,為什么要剪掉?很明顯,他有難言之隱,不想讓任何人知道其中的隱情。
但細(xì)讀這則日記你會(huì)發(fā)現(xiàn)第一句“上午池上來(lái)診”,十四日之后的十五日、十六日兩天周作人的日記中都有“池上來(lái)診”的記錄。
池上是日本醫(yī)生,羽太信子生病一般都是請(qǐng)他來(lái)看,那幾天八道灣后院肯定氣氛緊張、壓抑,很可能羽太信子情緒激動(dòng),受到了什么刺激,和周作人說(shuō)了什么話以后精神變得恍惚,癔癥的老毛病又發(fā)作了。
我們從時(shí)間上可以推斷,“過(guò)去的事”發(fā)生在七月十四日以前,其后幾天,信子很可能處于病中,情緒不穩(wěn)定,她是斷斷續(xù)續(xù)、一點(diǎn)一點(diǎn)向丈夫透露實(shí)情的,至十八日,周作人得知了大部分所謂的真相,怒不可遏,于是憤而采取行動(dòng),與大哥果斷絕交。七月十九日,他在日記中有“寄喬風(fēng)、鳳舉函。魯迅函”的記載。給魯迅的函就是絕交信。
十四日,魯迅改在自己屋里吃飯,這是一件看起來(lái)相當(dāng)嚴(yán)重的事,三天里他卻沒(méi)有問(wèn)為什么?是不太清楚發(fā)生了什么事?還是有所預(yù)料,靜觀事態(tài)的發(fā)展?從十九日魯迅接到絕交信的反應(yīng)看,后者的可能性大一些。
3.魯迅的異常反應(yīng)
魯迅的反應(yīng)是不解釋?zhuān)粶贤ǎR不停蹄,選擇逃避,匆匆忙忙托人為其找房,決定盡快搬出八道灣。周作人的信里沒(méi)說(shuō)讓他搬出去,只說(shuō)“以后請(qǐng)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lái)”,是魯迅自己做的這種決定。
八天后的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往磚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書(shū)籍入箱”,那幾天忙于整理書(shū)籍衣物后,八月二日下午,魯迅便“攜婦遷居磚塔胡同六十一號(hào)”。
周作人得知大哥搬走,只在日記中記了一筆:“下午L夫婦移住磚塔胡同。”L指的就是魯迅。
從收到絕交信到搬離八道灣,兄弟倆沒(méi)有再做任何交流溝通,個(gè)中原因想必是心照不宣、各自清楚的,只用了十二三天的時(shí)間,魯迅便完成了從找房、看房、收拾東西、搬家的全過(guò)程,時(shí)間不可謂不倉(cāng)促。他苦苦經(jīng)營(yíng)、親自選中、精心修繕的八道灣周氏大宅門(mén)就因?yàn)樾值苓@樣一封絕交信而灰頭土臉、匆匆忙忙地離開(kāi)了。這至少說(shuō)明兄弟之間的矛盾已經(jīng)嚴(yán)重到了不可化解、水火不容的地步,魯迅在自己占有相當(dāng)產(chǎn)權(quán)的八道灣住不下去,必須搬離了。
此時(shí)魯迅的心情想必是復(fù)雜沉重、相當(dāng)痛苦的,其中的原因?qū)嵲陔y與人言。與周作人的決裂,是他人生經(jīng)歷中最沉痛的打擊。我們不知道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但是我們要問(wèn),為什么搬出去的不是周作人而是魯迅?房子是魯迅操持買(mǎi)的,歷盡周折,費(fèi)盡精力;他是主要的出資人,事實(shí)上擁有大部分的產(chǎn)權(quán)份額;找房、買(mǎi)房、修房,到千里之外的故鄉(xiāng)紹興接家人遷居北京,都是魯迅忙前忙后親力親為的,二弟周作人基本上是坐享其成。從情理上講,兄弟之間鬧矛盾住不到一塊,要搬出去的也應(yīng)該是二弟周作人一家。匆匆做此決定,僅僅是因?yàn)轸斞傅拇蠖葘捜荨⒛罴靶值苤閱幔吭蚩隙ㄒ冗@復(fù)雜得多。兄弟倆的矛盾已經(jīng)深到不能見(jiàn)面,不能溝通,不能在一個(gè)院里生活的嚴(yán)重地步,已經(jīng)激化到魯迅必須急匆匆地搬出八道灣。
直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八十歲高齡的周作人在與香港翻譯家鮑耀明的通信中才勉強(qiáng)談及此事,他解釋說(shuō):
昨日收到《五四文壇點(diǎn)滴》,謝謝。現(xiàn)已讀了十之八九,大體可以說(shuō)是公平翔實(shí),甚是難得。關(guān)于我與魯迅的問(wèn)題,亦去事實(shí)不遠(yuǎn),因?yàn)槲耶?dāng)初寫(xiě)字條給他,原是只請(qǐng)他不再進(jìn)我們的院子里就是了。
趙聰寫(xiě)的《五四文壇點(diǎn)滴》一書(shū)是香港友聯(lián)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版的,其中有一篇《魯迅與周作人》的文章,記載了兄弟失和的一些內(nèi)容,文章不長(zhǎng),重要的是這樣一段話:“許壽裳說(shuō)過(guò),他們兄弟不和,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據(jù)說(shuō)她很討厭她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
周作人此后又兩次在寫(xiě)給友人鮑耀明的信中基本上認(rèn)同作者引述許壽裳的說(shuō)法:兄弟失和的主要原因,是羽太信子討厭大伯哥魯迅,不愿意和他同住。至于為什么不愿意?周作人沒(méi)有說(shuō),他只說(shuō)當(dāng)初并沒(méi)有要把魯迅逐出八道灣的意思,事實(shí)上,即使他想這么做,魯迅硬是不搬,他也沒(méi)有辦法,因?yàn)榘说罏车姆慨a(chǎn)是全家共同買(mǎi)下的。
當(dāng)年購(gòu)買(mǎi)的八道灣十一號(hào)院,用現(xiàn)在的話說(shuō)是一處二手房,房款是三千五百大洋,中保人酬金,也就是中介費(fèi)一百七十五元,加上手續(xù)費(fèi)、改建裝修費(fèi)等共計(jì)大洋四千三百八十五元一角。這筆錢(qián)在當(dāng)年價(jià)值不菲,主要資金為變賣(mài)紹興周家新臺(tái)門(mén)老宅所得,加上魯迅和周作人多年的積蓄、貸款、朋友挪借等等,總之也是七拼八湊才買(mǎi)的房子。宅院的房產(chǎn)主寫(xiě)的是周樹(shù)人(魯迅)的名字,雖然房契寫(xiě)明房產(chǎn)共分為四份,母親魯瑞和三個(gè)兒子周樹(shù)人、周作人、周建人各占一份,但事實(shí)上魯迅是出資最多,出力也最多的,周作人沒(méi)有理由也沒(méi)有權(quán)力將他趕出去。魯迅急急忙忙搬走自然有他非搬不可的原因。
周作人的絕交信讓他的大哥措手不及,魯迅幾乎在八道灣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最后被迫“攜婦遷居”,搬了出去。
兄弟失和,對(duì)魯迅的打擊是巨大的,他的惡劣情緒長(zhǎng)期難以平復(fù)。這之后,他多次使用“宴之敖”“敖者”“宴敖”“敖”等為筆名,以發(fā)泄心中的積郁憤怒。他自己解釋說(shuō):“宴從門(mén)(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趕出來(lái)的。”他對(duì)弟媳羽太信子的怨恨始終難以釋?xiě)眩坦倾懶摹?
令人費(fèi)解的是,一個(gè)日本女人、弟媳,憑什么要和大伯哥水火不容,非要將他“趕”出家門(mén)呢?而魯迅偏偏又不做回應(yīng)反擊,任人擺布欺負(fù)?
4.移居磚塔胡同
家庭的突然變故,讓魯迅措手不及,他沒(méi)有時(shí)間也沒(méi)有財(cái)力在短時(shí)間內(nèi)重新購(gòu)房,只好通過(guò)熟人借住別人在磚塔胡同六十一號(hào)的三間空房。
搬出八道灣之前,妻子朱安的安置讓魯迅頗費(fèi)心思。帶她出去共同生活,魯迅心里是極不情愿的,他寧可獨(dú)身,也不想單獨(dú)面對(duì)名義上的妻子,于是提出讓朱安留在八道灣陪母親,或是回紹興娘家,由他出錢(qián)供養(yǎng)。這兩種選擇都是朱安無(wú)法接受的,丈夫搬出去,她自然應(yīng)該跟著走,燒飯、縫補(bǔ)、洗衣、掃地、做家務(wù)……照顧丈夫的日常起居。無(wú)奈之下,魯迅只好帶著她一同住到了磚塔胡同,但夫妻關(guān)系沒(méi)有得到改變,兩個(gè)人仍舊各居一室。
這是魯迅情緒最為低落的時(shí)期,二弟的絕情反目對(duì)他造成了致命的打擊,在沒(méi)有愛(ài)情的生活中,他對(duì)親情看得很重,在所有親人中,除了母親,魯迅與小他四歲的周作人的感情最好,兩個(gè)人同樣在紹興三味書(shū)屋、南京水師學(xué)堂讀過(guò)書(shū),同樣在日本留過(guò)學(xué),同樣在北京工作寫(xiě)作交友,長(zhǎng)期吃住在一起,共同的愛(ài)好志趣、共同的觀點(diǎn)、共同的朋友、共同的事業(yè),周作人幾乎是踏著他的腳步一路走來(lái)。
對(duì)弟媳羽太信子,魯迅也付出了過(guò)多的關(guān)照。一九〇八年春天,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學(xué)期間,與許壽裳等五人租住在東京的一處宅子,取名為“伍舍”。二十歲的羽太信子當(dāng)時(shí)是他們雇來(lái)打理雜務(wù)的下女,后與周作人戀愛(ài)結(jié)婚。信子家在日本屬于社會(huì)底層,嫁給周家后,她的娘家得到過(guò)周氏兄弟許多幫助。尤其是魯迅多次給信子家寄錢(qián)資助,和羽太家長(zhǎng)期保持著通信聯(lián)系。
據(jù)魯迅日記記載,截止到一九一九年與羽太信子通信二十四封,寄錢(qián)二十次。就連買(mǎi)了八道灣十一號(hào)院的房子以后,考慮到信子、芳子姐妹都是日本女人,魯迅特意把院里最好的房子讓給她們,并進(jìn)行了日式的改建裝修,他對(duì)二弟周作人夫妻應(yīng)該說(shuō)是仁至義盡、恩重如山。沒(méi)想到這次卻禍起蕭墻,兄弟之情斷絕。這種突然的變故,前因后果,魯迅肯定進(jìn)行了長(zhǎng)久地反思、痛苦地反思,好好的一對(duì)兄弟分道揚(yáng)鑣,鬧到分手,以后親人怎樣相處,外人又會(huì)怎么看?更令他苦悶不堪的是心里的隱痛還沒(méi)法與外人言說(shuō)。魯迅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幾個(gè)星期后,他的肺病發(fā)作,病情嚴(yán)重,只能吃流質(zhì)食物,前后為時(shí)一個(gè)半月之久。這時(shí)的他,可以說(shuō)是“貧病交加、情緒低沉”。
因事發(fā)突然,魯迅是在毫無(wú)準(zhǔn)備的情況下被逐出了八道灣,手里沒(méi)有多少積蓄,心情郁悶,情緒低落,一時(shí)也找不到合適的房子。倉(cāng)促間通過(guò)熟人租住在磚塔胡同六十一號(hào)。熟人是他們的同鄉(xiāng)、學(xué)生許欽文的四妹許羨蘇,她一九二〇年從紹興到北京報(bào)考學(xué)校,一度住在八道灣,與周家兄弟及全家關(guān)系很好。她的同鄉(xiāng)、同學(xué)俞芬?guī)е隙岱肌⒗先嵩褰忝茫≈赣H朋友的房子,院子里有三間空房。魯迅通過(guò)許羨蘇幫助聯(lián)系租住下來(lái),月租八塊錢(qián)。
磚塔胡同離八道灣不遠(yuǎn),但房子逼仄破舊,三間房的面積加起來(lái)只有二十多個(gè)平方米。母親魯瑞那年六十六歲,身體還好。她喜歡朱安,心疼兒子,在八道灣身邊連個(gè)說(shuō)話的人都沒(méi)有,頗感寂寞孤獨(dú),便時(shí)常到磚塔胡同來(lái)坐坐,有時(shí)也住在這里。三間小房,屋里擠得連放書(shū)的地方都沒(méi)有。顯然,這里并非久棲之地,作為長(zhǎng)子,魯迅覺(jué)得應(yīng)該奉養(yǎng)母親。
不久魯迅就在不停地找房子。據(jù)這之后三個(gè)月的日記中記載,他外出看房子多達(dá)二十余次十幾處。“小雨,午后與李姓者四近看屋。下午大雨。”“下午與秦姓者往西城看屋兩處。”“下午同楊仲和看屋三處,皆不中意。”等等等等。有時(shí)得了病,發(fā)著燒,或有其他事情,但也不得不四處找房子。十月三十一日,終于選定了阜成門(mén)內(nèi)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hào)房屋,房?jī)r(jià)八百元,雖不算貴,但是破爛不堪。魯迅親自設(shè)計(jì),找人施工,事無(wú)巨細(xì),奔波操勞,花了一千多塊錢(qián)重新加以改建翻修。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魯迅攜妻子朱安遷入新居。
5.兄弟反目 大打出手
失和事件發(fā)生十個(gè)月以后,魯迅有了新的住所,生活逐漸安定下來(lái),情緒也稍加平復(fù),便回到八道灣去取東西,沒(méi)想到和周作人之間又爆發(fā)了一場(chǎng)更為激烈的沖突。
魯迅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的日記中寫(xiě)道:
……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shū)及什器,比進(jìn)西廂,啟孟及其妻子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lái),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yǔ),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shū)、器而出。
這是兄弟失和后時(shí)隔十個(gè)月,魯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八道灣舊宅,肯定回的是自己的房間,絕不可能再到后院。
沒(méi)想到周作人聽(tīng)說(shuō)后與妻子信子趕到魯迅的房間大吵大鬧,還叫來(lái)了朋友。吵鬧中,周作人甚至抄起桌上的一個(gè)一尺高的獅形銅香爐朝魯迅頭上打去。幸虧由別人搶下,否則后果不堪設(shè)想。
當(dāng)時(shí)搶下香爐唯一在場(chǎng)的人是川島(章廷謙),他是魯迅和周作人共同的朋友,當(dāng)年二十二歲的他剛從北京大學(xué)畢業(yè),留校任校長(zhǎng)辦公室外交秘書(shū),并兼哲學(xué)系助教,此時(shí)正借住在八道灣周宅的一間空房。后來(lái)他在《弟與兄》一文中回憶說(shuō):
其時(shí),我正在八道灣宅的外院(前后共有三個(gè)院子)魯迅先生曾經(jīng)住過(guò)的房子里。就在那一日的午后我快要去上班的當(dāng)兒,看見(jiàn)魯迅先生來(lái)了,走進(jìn)我家小院的廚房,拿起一個(gè)洋鐵水杓(勺),從水缸中舀起涼水來(lái)喝,我要請(qǐng)他進(jìn)屋來(lái)喝茶,他就說(shuō):“勿要惹禍,管自己!”喝了水就獨(dú)自到里院去了。過(guò)了一會(huì),從里院傳出一聲周作人的罵聲來(lái),我便走到里院西廂房去。屋里西北墻角的三角(腳)架上,原放著一個(gè)尺把高的獅形銅香爐。周作人正拿著要砸去,我把它搶下了,勸周作人回到后院的住房后,我也回到外院自己的住所來(lái),聽(tīng)得信子正在打電話。是打給張、徐二位的。是求援呢還是要他們來(lái)評(píng)理?我就說(shuō)不清了。
川島不懂日語(yǔ),周作人夫婦“罵詈”的內(nèi)容聽(tīng)不明白,等羽太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及周作人的朋友張鳳舉、徐耀辰趕來(lái)以后他已經(jīng)退場(chǎng)了。
魯迅幾乎受到了圍攻,先是羽太信子謾罵,周作人幫腔,后又招來(lái)羽太重久、張鳳舉、徐耀辰助陣。張、徐二人都曾留日,當(dāng)時(shí)在北京大學(xué)擔(dān)任國(guó)文系教師,和周氏兄弟多有交往,與周作人的往還更密切一些,羽太信子說(shuō)的日語(yǔ),他們都能聽(tīng)懂。
關(guān)于此事,魯迅沒(méi)有再留下相關(guān)文字,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中說(shuō):
后來(lái)魯迅也曾經(jīng)告訴我,說(shuō)那次他們氣勢(shì)洶洶,把妻舅重久和他們的朋友找來(lái),目的是要給他們幫兇。但是魯迅說(shuō),這是我們周家的事情,別人不要管。張徐二人就此走開(kāi)。信子捏造魯迅的“罪狀”,連周作人自己都要“救正”,可見(jiàn)是經(jīng)不起一駁的。當(dāng)天搬書(shū)時(shí),魯迅向周作人說(shuō),你們說(shuō)我有許多不是,在日本的時(shí)候,我因?yàn)槟銈兠吭轮豢苛魧W(xué)的一些費(fèi)用不夠開(kāi)支,便回國(guó)作事來(lái)幫助你們,及以后的生活,這總算不錯(cuò)了吧?但是周作人當(dāng)時(shí)把手一揮說(shuō)(魯迅學(xué)做手勢(shì)):“以前的事不算!”
(許廣平著《魯迅回憶錄》,長(zhǎng)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
如果許廣平的這段記載準(zhǔn)確無(wú)誤的話,以我的理解,這哪像是出自魯迅之口,哪像是魯迅在激憤之下的語(yǔ)言。
受到誤解,事過(guò)十個(gè)月以后在自己的房間取東西,又受到周作人夫妻倆無(wú)端的辱罵,羽太信子述“罪狀”“多穢語(yǔ)”,周作人幫腔“救正”,甚至暴力相向。兩個(gè)人蠻橫無(wú)理、尋釁滋事,魯迅應(yīng)該義正詞嚴(yán)、逐字逐句地加以痛斥反駁才對(duì),但是卻莫名其妙、軟弱無(wú)力地說(shuō)出這樣的話,似乎“回國(guó)作事來(lái)幫助你們,及以后的生活”,就能抵消對(duì)方指責(zé)的“罪狀”,顯得有些底氣不足,缺乏聲討的氣勢(shì)。
魯迅對(duì)張鳳舉、徐耀辰說(shuō)道:“這是我們周家的事情,別人不要管。”他要顧及顏面、名譽(yù),不愿意讓外人了解實(shí)情,更不用他們來(lái)判明是非。如果真有什么不愿意讓外人知道的隱情,周作人自然也是當(dāng)事人之一,他招來(lái)外人助陣,不怕家丑外揚(yáng),我理解,至少在周作人看來(lái),錯(cuò)的一方是大哥。而魯迅這時(shí)的表現(xiàn)超出人們的想象,哪里還找得到一點(diǎn)“橫眉冷對(duì)”、頑強(qiáng)不屈的影子。
同一天周作人的日記記得很簡(jiǎn)略:“下午L來(lái)鬧,張徐二君來(lái)。”L即魯迅,張、徐即朋友張鳳舉、徐耀辰。“來(lái)鬧”,顯然不是事實(shí),魯迅是回來(lái)“取書(shū)及什器”,要鬧早就鬧了,何至于要等到十個(gè)月以后。
魯迅的摯友許壽裳后來(lái)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也提到過(guò)此事:
說(shuō)起他的藏書(shū)室,我還記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這所小屋(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hào))既成以后,他就獨(dú)自個(gè)回到八道灣大宅取書(shū)籍去了。據(jù)說(shuō)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shū)遠(yuǎn)遠(yuǎn)地?cái)S入,魯迅置之不理,專(zhuān)心檢書(shū)。一忽兒外賓來(lái)了,正欲開(kāi)口說(shuō)話;魯迅從容辭卻,說(shuō)這是家里的事,無(wú)煩外賓費(fèi)心。到者也無(wú)話可說(shuō),只好退了。這在取回書(shū)籍的翌日,魯迅說(shuō)給我聽(tīng)的。我問(wèn)他:“你的書(shū)全部都已取出了嗎?”他答道:“未必。”我問(wèn)他我所贈(zèng)的《越縵堂日記》拿出了嗎?他答道:“不,被沒(méi)收了。”
這件事?lián)S壽裳說(shuō)是魯迅轉(zhuǎn)天告訴他的,沒(méi)有提及周作人要用銅香爐砸他,而是說(shuō)用書(shū)遠(yuǎn)遠(yuǎn)投擲,這個(gè)細(xì)節(jié)也許存在。但川島的說(shuō)法更為準(zhǔn)確,他是當(dāng)時(shí)沖突發(fā)生前半場(chǎng)唯一的見(jiàn)證人,后半場(chǎng)張鳳舉三人到來(lái)時(shí)他已然退場(chǎng)了。也許是兩個(gè)動(dòng)作兼而有之,先用香爐砸被人奪下,后來(lái)又用書(shū)本砍,也未可知。總之,周作人對(duì)大哥的行為可謂暴烈無(wú)情。
直到晚年,周作人才在《知堂回想錄》(一四一)中反駁許壽裳的說(shuō)法:“這里我要說(shuō)明,徐是徐耀辰,張是張鳳舉,都是那時(shí)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賓,如許季茀(許壽裳)所說(shuō)的,許君是與徐張二君明白這件事的內(nèi)容的人,雖然人是比較‘老實(shí)’,但也何至于造作謠言,和正人君子一轍呢?”
許壽裳已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在臺(tái)灣慘遭殺害,時(shí)過(guò)境遷,二三十年后周作人想起這事還是憤憤難平,火氣不減。當(dāng)然,他說(shuō)的所謂“謠言”,不可能是指許壽裳“造作”,矛頭自然是另有所指。
6.失和原因“經(jīng)濟(jì)說(shuō)”
是什么樣的深仇大恨讓一向平和沖淡、溫文儒雅的周作人大發(fā)雷霆、情緒失控,對(duì)有恩于他的大哥不依不饒,大打出手,甚至用香爐(或書(shū)本)相砸呢?事情已經(jīng)過(guò)去了十個(gè)月,按照常理,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兩個(gè)人這時(shí)應(yīng)該已經(jīng)冷靜下來(lái),魯迅又在失和之后做出了難以想象的讓步,主動(dòng)搬出了八道灣。周作人的火氣應(yīng)該逐漸消減才對(duì),況且八道灣并不是周作人的私宅,房產(chǎn)的份額魯迅占有一定的比例,人家回家來(lái)取東西,回的是自己的家,又沒(méi)有到你的后院來(lái),周作人為什么糾纏不休,追過(guò)來(lái)相逼吵鬧,甚至動(dòng)武。肯定是在這期間羽太信子不知又說(shuō)了什么對(duì)魯迅不利的話,信子的枕邊風(fēng)讓周作人對(duì)大哥的仇恨越積越深,以至忍無(wú)可忍,怒不可遏了。
到底兄弟之間發(fā)生了什么?羽太信子到底吹的是什么枕邊風(fēng)?我們不得而知,也不好妄加揣測(cè)。兄弟失和事件成了一樁迷案。
由于當(dāng)事人及目擊者不置一詞,引來(lái)許多學(xué)者的猜測(cè)。盡管眾說(shuō)紛紜,但是有一點(diǎn)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兩人的絕交不是出于政治立場(chǎng)、文學(xué)觀念和為人原則等問(wèn)題引發(fā)的,而是因?yàn)榧彝ッ芩隆?
魯迅的三弟周建人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說(shuō),兩個(gè)人的分手,“不是表現(xiàn)在政見(jiàn)的不同,觀點(diǎn)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間的糾紛。”
至于是什么家庭糾紛,周建人沒(méi)有說(shuō),也許他不清楚,也許他不愿意說(shuō)。反常的是,魯迅生前寫(xiě)給他的三百多封私信至今一封也沒(méi)有留下。
兄弟失和的前因后果、來(lái)龍去脈,除了兩位當(dāng)事人,三弟周建人應(yīng)該是比較清楚的。魯迅始終關(guān)愛(ài)照料著三弟,最后十年在上海時(shí)期,兩家的關(guān)系十分密切,走動(dòng)相當(dāng)頻繁,無(wú)論是當(dāng)時(shí)信談,還是后來(lái)面述,周建人了解的內(nèi)情相對(duì)較多,但他始終回避這個(gè)話題。魯迅寫(xiě)給他的信件涉及家庭情況的應(yīng)該占有一定比例,有的很可能涉及一些家庭成員的個(gè)人隱私,包括他自己的不愿公開(kāi)的內(nèi)容,這其中應(yīng)該也包括兩個(gè)哥哥周樹(shù)人(魯迅)、周作人的某些信息?這些信件是何等重要,但不管是出于什么考慮,保護(hù)自己或維護(hù)家人。三百多封信最后全被毀,只字未存,實(shí)在是讓人不可理解!
造成家庭糾紛的原因多種多樣,排除了政治原因,總體來(lái)說(shuō),最重要的無(wú)非是經(jīng)濟(jì)原因和感情原因。
來(lái)自魯迅方面的一些論者,將兄弟失和的原因主要?dú)w結(jié)為經(jīng)濟(jì)原因,認(rèn)為信子持家,揮霍無(wú)度,引起魯迅的不滿,信子便挑撥丈夫周作人與大哥反目。
魯迅的母親魯瑞曾對(duì)人說(shuō):“這樣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來(lái)想去,也想不出個(gè)道理來(lái)。我只記得:你們大先生(魯迅)對(duì)二太太(信子)當(dāng)家是有意見(jiàn)的,因?yàn)樗艌?chǎng)太大,用錢(qián)沒(méi)有計(jì)劃,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周建人在《魯迅與周作人:難以彌合的裂縫》一文中分析道:
在紹興,是由我母親當(dāng)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當(dāng)家。日本婦女素有溫順節(jié)儉的美稱(chēng),卻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卻真是個(gè)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氣派極闊,架子很大,揮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齊坤,還有王鶴照及燒飯司務(wù)、東洋車(chē)夫、打雜采購(gòu)的男仆數(shù)人,還有李媽、小李媽等收拾房間、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沒(méi)有這樣眾多的男女傭工。更奇怪的是,她經(jīng)常心血來(lái)潮,有時(shí)飯菜燒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房里趕緊包餃子;被褥用了一兩年,還是新的,卻不要了,賞給男女傭人,自己全部換過(guò)。這種種花樣,層出不窮。……魯迅看不過(guò)去,對(duì)周作人進(jìn)行規(guī)勸,無(wú)非是“花錢(qián)要有個(gè)計(jì)劃,也得想想將來(lái)”這一類(lèi)話,真也有周作人這樣的人,把好心當(dāng)惡意。有一次,周作人說(shuō)要把丈人丈母接到中國(guó)來(lái)同住,魯迅很不贊成,認(rèn)為多年來(lái)寄錢(qián)供養(yǎng)他們,已經(jīng)情至義盡了,今后可以繼續(xù)養(yǎng)老送終;他們還有別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國(guó)來(lái)了。
(《魯迅回憶錄》上冊(cè),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許廣平轉(zhuǎn)述魯迅對(duì)她說(shuō)過(guò)的話:
我總以為人不要錢(qián)總可以家庭和睦了罷,在八道灣住的時(shí)候,我的工資收入,全行交給二太太,連周作人的,不下600元,而每個(gè)月還總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shí)候借到手連忙回家。又看到汽車(chē)從家里開(kāi)出,我就想:我用黃包車(chē)運(yùn)來(lái),怎敵得過(guò)用汽車(chē)帶走的呢?……魯迅在八道灣住的時(shí)候,初時(shí)每月工資不欠,比周作人還多,又忠心耿耿的全部交出,兼以向朋友告貸,這樣的人,在家內(nèi)開(kāi)支是一個(gè)得力的助手,要得的。后來(lái)開(kāi)始欠薪,加以干涉到人事方面,就妨礙了主人的權(quán)威討厭起來(lái)了。
(許廣平《魯迅回憶錄》,長(zhǎng)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
魯迅之子周海嬰也說(shuō)過(guò)羽太信子:
講排場(chǎng),花錢(qián)如流水,毫無(wú)計(jì)劃。飯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廚房重做。她才生了兩個(gè)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說(shuō)也有六七個(gè),還不算接送孩子上學(xué)的黃包車(chē)夫。孩子偶有傷風(fēng)感冒,馬上要請(qǐng)日本醫(yī)生出診。日常用品自然都得買(mǎi)日本貨。由于當(dāng)時(shí)北平日本僑民很多,有日本人開(kāi)的店鋪,市場(chǎng)上也日貨充斥,應(yīng)該說(shuō)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滿意,常常托親戚朋友在日本買(mǎi)了捎來(lái)。因?yàn)樵谟鹛抛友劾铮毡镜娜魏螙|西都比中國(guó)貨要好。
(周海嬰《我與魯迅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
這里需要說(shuō)明的是,魯迅自己看病,也是找日本醫(yī)生,或德國(guó)醫(yī)生,從來(lái)不找中國(guó)醫(yī)生看中醫(yī),因少年時(shí)他的父親被中醫(yī)誤診騙錢(qián),不治身亡,魯迅一輩子對(duì)中醫(yī)深?lèi)和唇^。兩個(gè)弟媳都是日本人,孩子大人病了請(qǐng)日本醫(yī)生出診,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算不上揮霍。日本貨好像不僅是羽太信子覺(jué)得好,近百年后的不少中國(guó)人也承認(rèn)這個(gè)事實(shí)。
看不慣羽太信子的大手大腳、鋪張浪費(fèi),說(shuō)明魯迅對(duì)羽太信子持家理財(cái)有一定看法,療養(yǎng)則住在北京西山,有病則請(qǐng)日本醫(yī)生,購(gòu)物則買(mǎi)日本貨,家里還長(zhǎng)期雇著幾個(gè)傭人,但這絕不是造成他和二弟分手、恩斷情絕的主要原因,況且是周作人主動(dòng)和他決裂挑起事端,原因應(yīng)該出在周作人夫婦身上。
7.失和原因“失敬說(shuō)”
同為魯迅、周作人朋友的郁達(dá)夫在一九三八年寫(xiě)的《回憶魯迅》中說(shuō),兄弟失和的原因,除了經(jīng)濟(jì),還有羽太信子說(shuō)的“魯迅對(duì)她有失敬之處”:
在我與魯迅相見(jiàn)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消息,從祿米倉(cāng)的張徐二位聽(tīng)到了。原因很復(fù)雜,而旁人也終于不明白是究竟為了什么。但魯迅的一生,他與周作人氏,竟沒(méi)有和解的機(jī)會(huì)。本來(lái),魯迅和周作人氏哥兒倆,是住在八道灣的那一所大房子里的。這一所大房子,系魯迅在幾年前,將他紹興的祖屋賣(mài)了,與周作人在八道灣買(mǎi)的;買(mǎi)了之后,加以修繕,他們兄弟和老太太就統(tǒng)在那里住了。俄國(guó)的那位盲詩(shī)人愛(ài)羅先珂寄住的,也就是這一所八道灣的房子。后來(lái),魯迅和周作人氏鬧了,所以他就搬了出來(lái),所住的,大約就是磚塔胡同的那一間小四合了。所以,我見(jiàn)到他的時(shí)候,正在他們的口角之后不久的期間。據(jù)鳳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兄弟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shuō)魯迅對(duì)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shí)候?qū)ξ艺f(shuō):“我對(duì)啟明,總老規(guī)勸他的,教他用錢(qián)應(yīng)該節(jié)省一點(diǎn),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lái)。他對(duì)于經(jīng)濟(jì),總是進(jìn)一個(gè)花一個(gè)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huì)合起來(lái),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郁達(dá)夫在文章中除提到魯迅對(duì)他說(shuō)的話之外,還提到了張鳳舉他們的判斷:羽太信子說(shuō)魯迅對(duì)她有“失敬”之處。這當(dāng)然是她的一面之詞,有沒(méi)有失敬?失敬到什么程度?“清官難斷家務(wù)事”,外人實(shí)在是說(shuō)不清楚。
持“家庭經(jīng)濟(jì)說(shuō)”的基本上以魯迅的親友為主。
真的像人們說(shuō)的,兄弟失和是因?yàn)榻?jīng)濟(jì)糾紛造成的嗎?讓我們看看當(dāng)時(shí)八道灣周宅的經(jīng)濟(jì)狀況是怎樣的。
魯迅當(dāng)時(shí)買(mǎi)這所宅院,最初的想法是兄弟三人永不分家,把錢(qián)放在一起合用,有福同享,有難同當(dāng)。全家人從老家紹興遷到北京后,大哥魯迅在教育部當(dāng)僉事,月薪三百大洋,有時(shí)欠薪;老二周作人在北京大學(xué)當(dāng)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大洋,兄弟倆還有一些稿費(fèi)、講課費(fèi)等收入,只有老三周建人初期沒(méi)有工作,搬到北京近兩年后,到上海商務(wù)印書(shū)館工作,月薪六十大洋。周宅的家庭成員情況是:三兄弟供養(yǎng)老娘,魯迅和朱安兩口,周作人一家五口,周建人一家四口,全家雇傭幾個(gè)幫工。
到北京以后,母親魯瑞不習(xí)慣北方生活,表示不掌家。朱安性格軟弱,與世無(wú)爭(zhēng),與魯迅的感情不和,家里的財(cái)政大權(quán)落到了羽太信子手里。信子是日本媳婦,日本的生活習(xí)慣、飲食習(xí)慣,魯迅、周作人兄弟、信子、芳子姐妹以及孩子們都能接受。從三個(gè)獨(dú)立家庭的收入支出而言,魯迅一家貢獻(xiàn)最多,開(kāi)支最小;周作人收入第二,開(kāi)支最大;周建人收入最少,開(kāi)支中等。總體來(lái)講,全家人搭伙過(guò)日子,魯迅的付出最多,信子應(yīng)該是滿意和接受的。周建人收入雖少,但芳子不僅是弟妹,也是羽太信子的親妹妹,經(jīng)濟(jì)上多負(fù)擔(dān)一些是說(shuō)得過(guò)去的。
在魯迅的傳統(tǒng)意識(shí)中,他的家庭觀念是大家庭,是以母親為主的兄弟三人的家族,不僅僅是他和朱安兩個(gè)人的小家庭,況且他長(zhǎng)期和朱安感情不和,終年分居。魯迅回國(guó)以后,身為長(zhǎng)子、大哥,承擔(dān)起的是撫養(yǎng)大家庭的義務(wù),甚至?xí)r常接濟(jì)弟媳羽太信子日本的娘家,信子的父親、弟弟、妹妹在經(jīng)濟(jì)上都得到過(guò)魯迅的資助,“魯迅除了負(fù)擔(dān)八道灣絕大部分家用之外,連日本人信子們的父親羽太家:每月家用的接濟(jì),兒子重久三次到中國(guó)和在日本不時(shí)需索以及軍營(yíng)的所需費(fèi)用,及第三個(gè)女兒福子的學(xué)費(fèi),也都是魯迅每月收到工資,即行匯出的。”(許廣平《魯迅回憶錄》,長(zhǎng)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
在魯迅收入少的時(shí)候沒(méi)有發(fā)生金錢(qián)上的矛盾,收入多了反而產(chǎn)生矛盾,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因?yàn)椋笆Ш褪录笔峭蝗槐l(fā)的,如果是因?yàn)榧彝ソ?jīng)濟(jì)問(wèn)題,它有一個(gè)逐漸積累的過(guò)程。周作人心里很清楚,魯迅對(duì)整個(gè)大家庭,包括對(duì)他個(gè)人在經(jīng)濟(jì)上的貢獻(xiàn)是最多的,他應(yīng)該心存感激才對(duì),魯迅即使對(duì)家庭開(kāi)支有意見(jiàn),周作人即使再糊涂,也會(huì)理解,也應(yīng)該理解,絕不至于為此事怒火中燒,也絕不至于為此事絕情絕義。
8.到底發(fā)生了什么
兄弟失和如果不是家庭經(jīng)濟(jì)問(wèn)題,那另一個(gè)原因似乎只能是感情問(wèn)題,是妻子與大哥的關(guān)系問(wèn)題。周作人這一方主要持感情說(shuō)。
一種說(shuō)法是魯迅偷看了弟媳羽太信子洗澡或聽(tīng)窗。
一九七五年,川島對(duì)魯迅博物館工作人員說(shuō):“魯迅后來(lái)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謠說(shuō)魯迅調(diào)戲她。周作人老婆對(duì)我還說(shuō)過(guò):魯迅在他們的臥室窗下聽(tīng)窗。”他為魯迅辯誣說(shuō):“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八道灣后院的房屋,窗戶(hù)外有土溝,還種著花卉,人是無(wú)法靠近的。”說(shuō)到周作人夫人與魯迅關(guān)系緊張的原因時(shí),川島則說(shuō):“主要是經(jīng)濟(jì)問(wèn)題。她(羽太信子)揮霍得不痛快。”
“聽(tīng)窗”一說(shuō)像川島說(shuō)的是“造謠”“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不僅因?yàn)榇巴庥袦希€種著花,人無(wú)法靠近,還因?yàn)槿绻腥寺?tīng)窗被發(fā)現(xiàn),屋里的周作人夫婦應(yīng)該都能察覺(jué),用不著羽太信子事后告訴丈夫,何來(lái)周作人絕交信中說(shuō)的“我昨天才知道”一語(yǔ)。
“窺浴”一說(shuō),魯迅之子周海嬰在《我與魯迅七十年》中辯駁道:
父親與周作人在東京求學(xué)的那個(gè)年代,日本的習(xí)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進(jìn)進(jìn)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說(shuō),我們中國(guó)傳統(tǒng)道德觀念中的所謂“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臨近世紀(jì)末這風(fēng)俗似乎還保持著,以致連我這樣年齡的人也曾親眼目睹過(guò)。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訪問(wèn),有一回上廁所,看見(jiàn)里面有女工在打掃,她對(duì)男士進(jìn)來(lái)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間有門(mén)的馬桶去方便。據(jù)上所述,再聯(lián)系當(dāng)時(shí)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對(duì)方的住處原是尋常事,在這種情況之下,偶有所見(jiàn)什么還值得大驚小怪嗎?退一步說(shuō),若父親存心要窺視,也毋需(無(wú)須)踏在花草雜陳的“窗臺(tái)外”吧?
周海嬰分析得有一定道理,但作為后人,這種辯解就顯得有點(diǎn)多此一舉,軟弱無(wú)力了,似乎認(rèn)同了“偶有所見(jiàn)”的說(shuō)法,接受了“窺浴”的觀點(diǎn)。
竊以為,“窗戶(hù)外”只是個(gè)距離問(wèn)題,看清沒(méi)看清與看沒(méi)看屬于不同性質(zhì)的問(wèn)題。是跨過(guò)溝還是在溝外側(cè),其實(shí)并不重要,院子里的瀉水溝想必也不寬,關(guān)鍵是看了沒(méi)有。
我們退一萬(wàn)步說(shuō),姑且認(rèn)為真的看了,真的發(fā)生了“窺浴”之事,就真的那么重要,真的讓周作人大光其火、絕情絕義嗎?
羽太信子是日本女人,就像周海嬰說(shuō)的:“日本的習(xí)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進(jìn)進(jìn)出出,相互都不回避。”
日本自古就有男女同浴的風(fēng)俗,貞節(jié)觀念也較中國(guó)婦女應(yīng)該更開(kāi)放一些。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學(xué)多年,對(duì)這些情況是了解的,不足為怪的。魯迅去世后,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里說(shuō):“魯迅一九〇四年往仙臺(tái)進(jìn)了醫(yī)學(xué)專(zhuān)門(mén)學(xué)校,有一次來(lái)信給我,大意說(shuō)氣候較寒,每日借入浴取暖,仙臺(tái)的浴池,男女之分,只隔著一道矮矮的板壁,同學(xué)們每每邊唱邊洗,有的人乃踏上小杌子,窺望鄰室。信中有兩句,至今我還記得的:‘同學(xué)陽(yáng)(佯)狂,或登高而窺裸女。’”那時(shí)的留學(xué)生,看女孩子洗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當(dāng)然,這和后來(lái)“兄弟失和”牽扯到的“窺浴”一說(shuō)沒(méi)有必然的聯(lián)系。
當(dāng)年的魯迅,時(shí)常、或者說(shuō)是每天都要到八道灣的后院周作人的住處去,或是吃飯,或是聊天,進(jìn)出隨意。日本人又相對(duì)講究衛(wèi)生,時(shí)值盛夏,羽太信子在后院屋內(nèi)洗澡,這種情況可能經(jīng)常發(fā)生,即使魯迅到后院無(wú)意中看到遮蔽不嚴(yán)的屋內(nèi)羽太信子在洗澡,即使駐足多看了兩眼,也并非十惡不赦的嚴(yán)重問(wèn)題。“食色,性也”,人之常情,偶見(jiàn)一個(gè)女人洗澡,又不是故意的,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退一步講,即使發(fā)生了這種事也不是不能解釋的。我們假設(shè),作為魯迅即使無(wú)意中真看見(jiàn)了弟媳在洗澡,無(wú)憑無(wú)據(jù),完全可以否認(rèn)。即使不加辯解,我相信,在日本生活過(guò)多年的周作人也不會(huì)懷恨在心,不依不饒。因?yàn)椋绻嬗写耸拢约旱睦掀乓灿邢喈?dāng)?shù)呢?zé)任,至少是門(mén)戶(hù)不嚴(yán),遮蔽不當(dāng)。為這點(diǎn)事,信子應(yīng)該不會(huì)小題大做、自取其辱,向丈夫哭訴。
除了上面這兩種說(shuō)法,很可能還有其他原因讓周作人耿耿于懷,難以原諒大哥。
至于“調(diào)戲”“失敬”等說(shuō)法沒(méi)有人知道是否存在,更沒(méi)有人知道具體內(nèi)容,至少周作人是相信了老婆羽太信子和他說(shuō)的話,認(rèn)為大哥做了有辱于他不可原諒的事,這種“家丑”難以啟齒,沒(méi)有相應(yīng)的證據(jù),憑空捏造誣陷,以魯迅的脾氣性格是絕不會(huì)善罷甘休的。
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我們無(wú)從知道,對(duì)于這件事,魯迅生前始終回避,不置一詞,與最親近的人也沒(méi)有詳細(xì)講過(guò),只是間接提及家庭經(jīng)濟(jì)糾紛,暗示自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對(duì)此事辯解。他在二十世紀(jì)六十年代與香港友人鮑耀明的通信中說(shuō):“大凡要說(shuō)明我的不錯(cuò),勢(shì)必先須說(shuō)對(duì)方的錯(cuò),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lái)做材料,這卻是不容易說(shuō)得好,或者不大想說(shuō)的,那么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shuō)了這些寒傖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mén)驅(qū)虎后門(mén)進(jìn)狼了么。”兩個(gè)人諱莫如深,為“兄弟失和”蒙上了一層神秘面紗。但是我們從僅有的一些史料中探幽發(fā)微,能否像郁達(dá)夫說(shuō)的:對(duì)他們反目的真實(shí)原因,猜度到一二成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