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以后,皇帝再未曾去過清思殿。
而“病美人”一說越為流傳開來,“清思殿”三字也被宮里人過度理解為只能懷思寵愛的地方。也不怪眾人對清思殿如此掛懷,主要是皇帝愿陪伴病妃一宿之事實屬前所未見。后宮女人多,茶后閑談也不乏談資。
不過,雖說流言紛紜,但言妃與黎妃暫且不論,側后竟也是關懷備至,時常送些精致小物或甜點類的。對于阮棲汐而言,只要不與皇帝交集過多,便是一種清閑,她擁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曾經事故的細節。
這日同往常一樣,言妃命人叫她去用晚膳,阮棲汐無奈地看向楊甜,道:“今日又省的你們去取膳了。”
說完,她略施粉黛就前往清言殿了。這些日子相處下來,她發現言妃果然別有一般女子情態,她對世俗女子所愛胭脂水粉提不起絲毫興趣,卻能在修建花草上養成一種溫柔嫻靜的氣質。她不喜談論各宮嬪妃長短,雖不喜黎妃,卻也能做到提及她時面不改色。
想來,言妃只是當真不喜黎妃這囂張的模樣吧。
膳后,二人相攜漫步梅林。
言妃忽而鄭重其事地問道:“我瞧著皇上怎生那日以后竟不再來看你了?這要不得寵就銷聲匿跡的做個無名人,但你這般被皇上偏愛過的人忽然間失了寵,其他妃妾的流言蜚語本宮怕你受不住啊。”
雖說阮棲汐對這些不甚在意,但言妃好心出言提醒,她也總不能拂了面子。
“臣妾明白。‘病美人’據說是那日請晨安時,田嬪提起的頭。那日去側后娘娘那請安之人皆是倚仗側后之人,這背后默許之意昭然若揭。且這一稱號與黎妃‘毒美人’一孱一強,怕是有心離間。”
言妃慚愧地笑了笑,道:“看妹妹這狀態沒被影響就好,還把后邊的人查了出來,倒是本宮多慮了。只是,妹妹還得掂量掂量,為何你姊姊到現在一點兒反應也沒有,照理說...”
她似乎意識到了自己在說什么,又出聲解釋道:“我這不是在離間你們姊妹的關系啊,妹妹多留個心眼就是了。”
隨后,她又扯開了話題,身為一個外人,對別人家事不宜多言。
雪色很美,不日就是春節了。想必側后已經開始著手置辦家宴事宜了,聽說多了皇親國戚,卻從未見過,也不知是何品行。
忽的想起許久沒見袁夢了,黎妃那日見狀以后當真不在派遣袁夢來污濁人眼了。
可這并不是阮棲汐想要的,在宮里唯有袁夢是突破口。
夜里,沈公公送來一封信箋,是阮浩楠托帝君給她的。宮里的規矩,不許后宮前朝之人私相授受。而顧念她狀況不佳,皇帝倒也是準了這信。其實她一直不知,為何皇帝會額外看好她家。若說戰場殺敵,父親早在十年前就開始隱退了,哥哥才上戰場不久,也談不上赫赫戰功,更別說黎妃之弟棄武從文,是阮府世代武將中唯一一個從文的,如今也不過爾爾,沒混出什么功績。
信箋上的內容從簡,先言家中一切無恙,自己近日也停留家中,期望查出一些結果。而之后一句話卻讓阮棲汐一個機靈,他說父親如今似乎也在查著往事,有私下調遣人去將那日指證娘親傷人的丫鬟找出來。
阮棲汐眉頭一皺,這人不正是袁夢嗎,她的問題果然很大!只是,她不明白父親為何會突然調查這事,果然,人只有失去了才能知曉珍惜嗎,現在察覺了不對勁兒。她諷刺地勾唇,雙指夾著信箋燒于火燭之中,入眠。
翌日,阮棲汐喚來了楊翎,道:“跟姐姐說一聲,我覺著袁夢機靈,看姐姐舍不舍得割舍一個婢子給我。”
楊翎駭然,問道:“奴婢覺得這不妥,咱們一來就要了她的心腹。先別說在府里時黎妃與小主就不多親近,現黎妃娘娘正在向小主示好,咱也得碼著一個度。”
阮棲汐沉吟片刻,她確實有些著急了,再過些時段也罷。她又道:“我不喜歡‘病美人’一說,總該換個叫法了。”
楊翎疑惑地看著她,她卻并沒有多說的意思,這搞得楊老媽子又開始緊張了。
下午時分,側后叫眾人齊聚一堂商討春節瑣事。雖說是商討,其實大多都由側后拿了主意,僅剩一些飯后甜點,禮樂之類的瑣事交談交談了。
眾位齊聚一堂,較第一次見面,低階嬪妃對阮棲汐的恭敬已經變得十分敷衍,更有甚者直接在底下毫不掩蓋聲音地談論起“病美人”。黎妃一記冷眼掃過去之處無人再敢多嘴。
“這次本宮想著往日歌姬舞姬唱跳十分無趣,也沒幾個人會看,不知妹妹們可有毛遂自薦愿意一展風姿?這也是皇上的意思,表現優異有賞!”此刻談及歌舞宴,側后說道。
“這在座姐妹想來有何才華早已被皇上知曉,多少都是無趣的。這瀟貴人唯一一次侍寢就身體不適不能在皇上面前嶄露頭角,這次的機會姐妹們就不多爭奪了,讓給瀟貴人就是。”嫻昭儀掩嘴笑道。
田嬪當即隨嘴道:“那是,側后娘娘就把她名字記上去吧。”她正損得開懷,卻冷不丁地收到側后的眼神警告,她不解,一個什么都不是的貴人為何會如此招側后忌憚。想歸想,她還是退出了嘲諷的行列。
“病美人,你啞巴了?”嫻昭儀嫌惡道。
阮棲汐眼神戲謔地看向嫻昭儀,不緊不慢道:“臣妾不曾想皇上召娘娘侍寢純粹是想看娘娘表演,不知娘娘有何擅長呢?”
說完,引來下邊一陣細碎的笑聲。
嫻昭儀黑了臉,氣的站起身:“你胡說什么呢,信不信本宮告你以下犯上?”
阮棲汐像看傻子似的看了她一眼,接著又屈膝道:“臣妾不敢。”
側后沒有出聲,黎妃和言妃卻同時出聲喚嫻昭儀,這種默契,言妃不喜,她便禮讓黎妃先說。
黎妃冷語道:“我與側后言妃尚在,豈容你在這自稱‘本宮’造次?還不跪下?瀟貴人先起,不必搭理粗婢。”說完,黎妃看向側后,問道:“娘娘認為呢?”
雖是問候,語氣卻絲毫不帶商量。側后也沒反駁什么,而是說道:“既犯了錯,妹妹不必留著她礙眼,還不退下?”
嫻昭儀還沒從這反差中緩過來,感激地看了一眼側后就離開了。
而側后的視線在黎妃與阮棲汐之間來回打轉,心中已有定數。
“現今看來,黎妃素日嬌蠻,卻是十分護著妹妹,想來這就是血緣的關系吧。”
黎妃不置可否,而是關切地看向阮棲汐,問道;“何妨?”
阮棲汐禮貌地回笑:“多謝姐姐出手以助,以及側后娘娘的秉公執事。”
側后頷首一笑,又看向蕓蕓眾人,問道:“各位妹妹當真沒有愿意大展身手的嗎?”
氣氛一片死寂,阮棲汐低頭侍弄手中茶盞,良久才悠悠出口道:“方才各位姐姐多有好奇,臣妾也不好讓二人失望了不是。臣妾愿意以琴一首活躍活躍氣氛。”
在座之人對她的主動請纓感到意外,許是有人先發聲了,底下坐著的人也躍躍欲試起來。當即又有包括田嬪在內的三人提出愿以略盡綿薄之力為帝君爭取一些臉面,畢竟家宴上的人皆為皇族,家宴辦好了也是給皇帝長臉。
側后如釋重負地笑了,頗為感激地說道:“那就有勞各位妹妹近期加以努力了,定會得到皇上的賞識。”
之后,眾人各自散了。黎妃趕忙走到阮棲汐身側,道:“妹妹終于知道露一手了,本宮還以為妹妹是想自此就隱匿下去,這可是擔心了許久呢。只是,昔日在府中從未聽聞妹妹善于琴藝,不若一舞,姐姐瞧著妹妹舞姿甚好,為何不以此奪人眼球呢。”
阮棲汐轉身看向她,一本正經地回道:“姐姐入宮之時妹妹尚小,妹妹兒時所愛隨著年歲增長亦能有所變化,姐姐只管信著妹妹就好。”
黎妃只能無奈地一聲嘆息,不再多加念叨,目視前方,只見言妃只身一人行進。
時光荏苒,稍縱即逝,轉眼就到了家宴當日。
夜幕降臨,王爺王妃皆已就位,各宮嬪妃也陸陸續續到齊,只差皇帝與側后尚未見蹤跡。
宮廷禮樂已然奏響,底下一派喧嘩。
阮棲汐不著聲色地打量了一番庭院布置,十分有排面,每個人的位置都有著一定程度上的講究,位分越高的離帝君也越近。妃子與王爺等人分坐兩側,頗有一番分庭抗禮的架勢。
少焉,側后緊跟皇帝步伐進入。下邊瞬間鴉雀無聲,待帝君落座,一派恢弘之聲響起。
“臣(妾)恭請皇上圣安。”
“卿等免禮。”皇帝揮手道。
落座聲陸續響起,隨后又是一番寒暄,阮棲汐對此絲毫提不起興趣,整個過程都有些奄奄的,但想著今日她還得露一手,又不得不強撐眼皮。
其間,皇帝的目光不經意地掃向她這,見她這幅模樣,不由得覺得有些許好笑,而果不其然,他也笑出了聲。身旁的側后對此他十分敏感,見他今日好像很是開心,問道:“皇上有何喜事,不妨同臣妾一說。”
皇帝淡淡的收回目光,斂去笑意,道:“無事。”
側后納悶,遂著他剛才的視線看去,大抵是瀟貴人或是嫻昭儀,但嫻昭儀許久未曾受寵,想來也不會是她,況且...她的目光不經意地掃向了沈公公。
側后柔聲說道:“皇上,今日這瀟貴人可是有一番表演呢,皇上這就迫不及待了?”
陸晟焰蹙眉,淡淡地瞥了她一眼,不怒自威道:“愛妃也開始揣摩朕的意思了?”
側后就要起身告罪,卻被他摁住了肩膀,他道:“今日家宴,朕恕你無罪。今夜朕去黎妃那,你不必久候了。”
側后抿了抿唇,低頭應了一聲“嗯”。
心下雖有不快,但后宮中執事的人還是她,她很快整理好情緒面上帶笑地看向眾人:“今年家宴不同往日,往日皆是俗人上陣表演宮廷禮樂,不免枯燥。今日,幾位妹妹自甘上陣表現一番,也算是提前祈愿未來一年萬事順遂,國泰民安。”
當即底下一片叫好,側后鼓了鼓掌,當即一幅筆墨紙硯就被呈上,尤答應在側后眼神示意下款款起身。尤答應出生書法之家,筆墨的造化遠勝旁人,但盡管如此,在后宮里沒有依靠的她只能是底端的存在。
在眾目睽睽之下,她緊張地走到硯臺之前,提筆的那一刻,心中的緊張煙消云散。
一個“韶”字在眾人伸長了脖子想要一探究竟的好奇下逐漸完善,優雅地提筆,又優雅地放筆,侍女小心地立起宣紙,尤答應微微欠身,道:“臣妾祝皇上的江山百姓皆能美好永在。”
皇帝面上點了點頭,似是很滿意,心中卻想著字雖好看但少了些味道。想到這,他看向了言妃。
言妃能感受到他的目光,但她卻沒有什么想法,故而她視作不見。自她喪子以后,她失了寫字作畫的樂趣。
皇帝也沒強求她,但田嬪卻忽的想起,揚聲道:“臣妾記得言妃娘娘曾被譽為江南才女,臣妾有幸見過一回,不知較這尤答應如何。”
皇帝再次將目光轉向言妃,言妃這次無法再裝蒜了,慚愧道:“臣妾許久未曾提筆,想來是比不過各位妹妹的,田嬪就別說笑了。”
坐在一側的黎妃緊瑣眉頭,涼颼颼目光瞥向田嬪,但很快又收回,無人見得。
阮棲汐想著言妃不肯提筆想必是中間有些什么過往,遂出聲道:“言妃娘娘既要把風頭留給了嬪妾等人,那田嬪娘娘也可別辜負了這番好意。”
見阮棲汐處處幫襯著言妃,田嬪只覺得她像極了狗腿,但也沒有再提這事。
側后繼續主持著場面,照理來說,尤答應之后便該是阮棲汐了,但不想側后隨即又點到了謝婕妤。
正當阮棲汐感到疑惑時,一架琴被抬上,她怔怔地看著謝婕妤上座,那日側后才提及最好莫要重合表演,以彰顯宮嬪多才多德。但此刻,不禁未念及自己,謝婕妤也搶先一步表演了琴曲。
她質疑的目光看向側后,但側后像是毫無感覺般看著面前的表演。在座的嬪妃也多少有些察覺到不對勁兒了,因著這位次是品階從低到高的順序來的,莫不是為了給謝婕妤一展才能的機會,側后適才取消了瀟貴人的奏樂?
當下眾人心思各異,也有的人向阮棲汐投來同情的視線,外界情況悉數被阮棲汐視若無睹,她正襟危坐地聽著高山流水般的琴弦之音繞著大殿久久不散,直到結束,可謂是余音繞梁。
待眾人品味過來時,謝婕妤已然退下。黎妃見狀不妙,派周嬤嬤私下來通告:“黎妃娘娘說不知為何您的節目久久未被點名,特托老奴告知若是之后未被點名便也不要再行追究,若是再被提及就拿出驚鴻一舞。”
說完也不待阮棲汐有何回應就匆匆歸位,黎妃也全神貫注地盯著臺上。
“朕不是聽說瀟貴人也有所展示?”陸晟焰沉聲問道。
側后神秘地回道:“她自個兒請纓有一絕妙節目呢,臣妾便讓其壓軸了。”
陸晟焰沒多想,但表情也談不上多好,只叮囑道:“日后品階高低,不得有違。”
側后尊敬稱喏,又清嗓叫下一人。
沒有點到自己,阮棲汐心中說不出的感覺,其實今日她想要來一出,一是為了擺脫“病美人”一稱,二是為了時不時在皇帝面上露個臉,以免日后有求之時被遺忘得徹底。
她沒有放松下來,田嬪翩然起舞。阮棲汐心中不安的感覺愈發強烈,而身邊迎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正是才奏完曲子的謝婕妤,她勾唇嘲諷道:“妹妹如此積極,我特意請命側后娘娘把你調劑到最后,壓軸出場。妹妹可別讓姐姐失望啊。”
此刻一切都明了了,謝婕妤面色嘲弄,阮棲汐再是不愿多言此時也禁不住她的挑釁,毫不客氣地回道:“妹妹以為小孩家家的事情不會發生在后宮中,倒是不曾想姐姐如此孩童心性,當真是被皇上冷落久了,閑得幼稚。”
謝婕妤此刻心情很好,也沒有與她爭辯,而是說道:“你嘴硬吧,可別丟了皇室臉面才好。”
阮棲汐臉色確實說不上有多好看,言妃見謝婕妤小人得志的樣子也猜到了她的計謀,于是她低調地靠近側后,又低聲地說道:“娘娘,瀟貴人當初所言奏樂以活躍氣氛,可如今娘娘把她調后不說,這琴樂也被人搶先一步,不若消去瀟貴人的戲場。”
側后沒有因她的話而有所動容,而是一幅寬慰的語氣說道:“妹妹無需擔憂,瀟貴人還未開口,妹妹何必多慮。況且本宮方才當著眾人的面說道有四位妹妹要一展身手,如今怎能說無就無呢。”
言妃還想開口,側后卻已經面露不耐了。這件事情,側后定然脫不了干系。言妃坐回自己的位置,心中卻是有感。
后宮險惡,若是這一關過不了,那...
眼瞧著舞曲就要結束,這舞不得奏不得,她猶豫了小刻,低聲在楊翎耳邊吩咐的兩句。而又過了須臾,阮棲汐只身離開了宴席,經過言妃時低聲告知:“待會兒若是問及臣妾,煩請娘娘告知眾人臣妾前往更衣。”
言妃擔憂地應道,目視她遠去的背影。
三人皆為人中龍鳳,所展示也能算是上乘。許是有了前面精彩的開端,壓軸出場之人無疑引起了眾人的好奇。在側后從容不迫地說完最后一個人,底下開始了小聲議論。
三王爺此刻將眾人的疑惑提了出來,道:“這尊卑有別,側后娘娘將這瀟貴人排在最后,不知有何深意。”
側后清了清嗓子,語氣頗有些故弄玄虛:“這尊卑之別自是有,但家宴所圖的不過就是樸實中一點驚艷。之所以把瀟貴人排后,就是想讓諸位大開眼界。”
三王爺被勾起了興趣,道:“哦?那臣等可就在此候著了。只是不知這瀟貴人此刻在何處。”
聞聲,側后看向阮棲汐的位置,卻空無一人,正打算命人去找。一席瀲滟窄繡修身紅裙加身的女子大步邁入,手握翠劍。
殿堂上的所有人無不被她吸引住目光,陸晟焰捋了捋下巴,眼底興味乍然顯現。
阮棲汐執劍拱手示意之后,揚劍在空中留下一道道殘影,紅衣翠劍的色彩碰撞,吸引著男子沸騰熱血。而在凌空而上的過程中,她摒棄手中長劍,自袖口中出了一條紅菱,看準了角度揮揚過去,與殿上宮稠相接。與此同時,另一只手也揮出紅菱,纏繞上宮柱,僅僅依靠著紅菱的扶持,她腳踩紅柱飛快走壁,似是一朵血紅的花朵正盛開時。
也不知是誰,突然叫好。眾人也在此刻反應過來,忽的響起如雷貫耳的聲音。
花開花謝,她忽然一躍,落到陸晟焰前方不遠處,單膝下跪抱拳以道:“博君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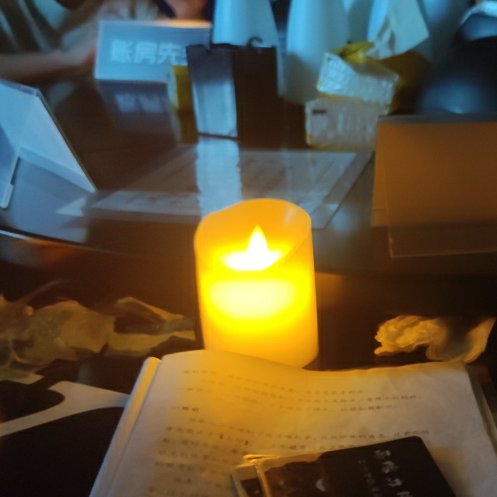
會笑的土撥鼠
因為是宮斗的嘛,所以有的時候可能會有很多鋪墊口水話,但我保證每章不論字數多少,一定有一個小爆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