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銘1978年生,香港人,祖籍杭州。
從他祖父那輩往上數,家中三十代以上都是在朝為官,最高做過明朝內閣大學士。
可謂是真正的書香門第之后,最末那代便是他祖父的爹杭州知府后來清朝沒落了,進入了民國軍閥混戰時期,他們家就是在那個時期全家遷移到了香港。
楊銘的父母是香港的商人,主要從事進出口貿易,家里條件還不錯環境優越,因此楊銘從小也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
由于世代處于書香門第之家,對中國的傳統文化也一直有所保留,他爺爺五個子女之中只有他父親經商。
他大伯香港大學中文系考古學教授,三叔是香港科技大學教師,小姑姑麻省理工大學心理學教授,還有一個是他小叔香港總督某處的一普通職員是他爺爺最看不起的。
不過揚銘最崇拜的,也最欣賞的是他大伯香港中文系考古教授,研究領域是中國神秘傳統文化,尤其對中國古代帝王的古墓感興趣。
楊銘也從小受到他大伯的熏陶,癡迷這種神秘的古墓文化,因此他大學也報考的考古系。
楊銘從小很是聰明,各科成績都是A+,讓他很順利的考上了香港的中文大學考古系,并且在大一時期便跟著他大伯一起做研究了,還是他大伯得力的助手。
在跟著他大伯學習期間他去過不少的國家參觀過不少的西方古代文化,其中有美國華盛頓博文館、英國的大英博物館,還有法國的盧浮宮。
讓他大伯最感興趣的還是埃及的金字塔,法老們那些奇怪的干尸和埃及奇怪的墓葬讓他大伯很是癡迷。
不過楊銘從小聽他祖父和爺爺給他講中國的傳統文化,講秦始皇時期,講秦始皇陵是多么的宏偉,講.......。
讓楊銘對這個他祖父和爺爺天天念叨的地方,他也很想去看看。
由于中國內陸在七八十年代,因為特殊原因并未對香港開放,因此他小的時候并未去過,他祖父一直想回杭州去看看,回自己的家可是當他去世時也沒如愿以償,他爺爺也是同樣如此。
楊銘覺得這是他祖父和他爺爺的遺憾他要替他們完成,因此在新中國改革開放后,他便先去了深圳、廣州。
由于自己要上學,當時開放也不是那么完全自由化,他也只能簡單參觀了一下內陸的深圳廣州,之后又回到香港繼續念書。
2001年,夏。
楊銘大學課程快修完了他正準備考研,他聽說北京大學的考古系研究生也對外招生,尤其對香港臺灣的學生有很多的優惠政策,校方為了兩岸的和諧友好也特別希望兩岸的學子們報考。
楊銘聽到這一消息后把這件事立即告訴了他大伯揚萬里,他大伯很是支持楊銘去內陸學習,不過楊銘的父母是不支持的。
楊銘不顧父母的反對質疑要去內地上學,而他父母只有楊銘這么一個獨子,兩夫婦一輩子辛苦打拼的公司好不容易在香港這個魚龍混雜的地方站穩了腳跟,
并且還有不錯的成績,心想著他們二人打好了基礎交給兒子管理,他們夫婦二人也可以享享福,準備去周游列國來個環球旅行,哪知楊銘并非按照他們的意愿去做。
讀書時讓他考金融系,學經濟,他非得去搞什么考古,跟著他大伯一天到晚鬼混,而他大哥楊萬里的兩個小孩反而去學了經濟系,并且還是海外名校畢業還做了香港銀行高層管理。
而自己的兒子卻變成了他哥哥的了,每天只知道跟著他哥哥屁股后面轉,楊銘的父母一氣之下斷了楊銘的生活來源,即使這也樣沒有阻止楊銘去內陸上學的決心。
楊萬里覺得他弟弟揚萬千做得有些過分了,便決定自己掏腰包讓楊銘去內地上學,正因為他大伯揚萬里的支持,楊銘索性從他家里搬了出來,在外單獨租了一套公寓。
他平時幫雜志社寫點報告什么的,偶爾給人做些翻譯,沒事時繼續幫他大伯做一些研究上的學術發表或者翻譯工作,這樣學校也會給他一些薪資,楊銘在外的收入便是做這些工作來維持他日常的開銷。
在一次研究有關一篇秦始皇兵馬俑的課題上,他大伯忽然想起了他爹離世之前交教他的那塊玉佩,之前他研究過,
不過由于自己事物繁忙并未仔細去發覺那塊玉佩究竟出自何處,想到楊銘想要考研到內陸,剛好又有一份關于秦始皇陵墓的研究要讓他去做,他索性便叫來了楊銘。
楊銘來到了研究室后他大伯揚萬里甩給他一份文件,上面寫著研究秦始皇兵馬傭是如何制作的課題。
楊銘只是在網上見過秦始皇兵馬傭的圖片真實的實物從未見過,他沒去過內地要如何研究。
楊萬里便簡單的跟他說了一些秦始皇時期的歷史,又說得了秦始皇陵兵馬俑。
“當時秦始皇嬴政從13歲即位時就開始營建陵園,
由丞相李斯主持規劃設計,大將章邯監工,修筑時間長達38年,工程之浩大、氣魄之宏偉,創歷代封建統治者奢侈厚葬之先例。”
.......。
他說道一半戛然而止,揚萬里本就從小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癡迷。
在1974年秦始皇陵墓被他一個同族兄長發現后,他也想參與其中去挖掘的。
可是由于兩地政治原因,這個心愿他最終沒有實現。
而經過一年多的才完全挖掘出來對外開放。
當時這個地宮很快成為了全球的熱門話題。
揚萬里一直想去參觀這個宏偉的地下建筑,但他是大學教授兼博士生導師事物繁重,一時脫不開身,
于是這次這個研究秦始皇兵馬傭的課題交給了他侄兒楊銘,順便告訴楊銘若是這件事做好了他進北京大學考古系讀研更近了一步。
楊銘聽著這件事第二日便去辦理去內陸所需要的一切手續,一個星期后他便回到香港中文大學他大伯的公寓。
由于他大伯癡迷于學術研究幾個月不回家是常用的事,楊銘也習慣了去大學公寓里找他來向他道別。
他大伯見楊銘要去西安秦始皇陵了,便親筆寫了封書信,讓他把信交給西安文物局處長,之后他大伯又從盒子里掏出一塊玉佩來交到楊銘的手中,
“這塊玉佩是我們楊家祖上傳下來的,誰也不知道這塊玉佩真正的來歷,你這次去內地幫我去探尋探尋。”
“楊家以前是有些祖傳的東西,因為特殊原因很多已經銷毀了,現在唯一就是這塊古老的玉佩,
聽說這塊玉佩是我們祖先一個偶然的機會得到的,楊家有個傳統的規矩,祖上的信物只能傳給長子,傳男不傳女,
而在我們這一代大多數對這些古玩意不敢興趣,我們家族中年輕一輩只有你喜歡這個,大伯我今年也五十多了離六十也不遠了,
研究這個東西估計也沒什么時間和精力了,這塊玉佩的未來你去探尋,我相信它絕非一塊普通的玉佩,
上面的文字是銘文我研究過這個文字跟秦朝有些關系,那些文字我是用萬倍放大鏡才看清楚的,還是一個女子名,因此你得好好帶著它別弄丟了。”
楊銘接過他大伯給他的那塊玉佩和那封書信便離開學校,回到出租公寓后他收拾了行李第二日一早便出發坐飛機離開了香港。
他先到的BJ,到BJ后先去故宮參觀一番,又去了北京大學打探了北京大學對香港學生招生的一些情況,在BJ逗留了幾日他便直接去了西安。
來到西安后他在當地城轉悠了幾天,體驗了一下這里的生活,之后他便直接去了西安文物管理局準備把他大伯的信交給那個文物管理處的處長。
他來到西安文物處管理處的處長辦公室,秘書很是熱情的接待了他,那處長走進來一看,原來是遠道而來的侄子,便伸出手來,他們相互握手后便坐了下來。
“聽萬里說你叫楊銘是他侄子。”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叫楊志發,和你還是同祖同宗。”
楊銘不明白什么是同祖同宗,他也不好問,于是他便從背包里拿出他大伯的信來交給了他,那揚志發打開信一看,原來那是封介紹信。
讓楊銘秦始皇兵馬傭在他那里做研究工作一段時間,為考北京大學考古系研究所做準備,那揚志發見揚萬里把自己的親侄子介紹到自己身邊做個研究員心里當然樂意看完此信后,
便對楊銘笑了笑,“以后你叫我發叔,我與你大伯年齡差不多,我們也經常書信來往,放心你來到我這里就當是自己家,明日我便幫你安排,一會兒叔帶你去吃這里當地的特色”
“楊銘聽得云里霧里的,那個不用了信我已經送到了,沒什么事的話我便走了。”楊銘想著他前幾日買了一張參觀秦始皇陵兵馬俑的票在今日下午四點便閉館他得抓緊時間去看。
揚志發見楊銘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但是信中只提了楊銘在內陸沒什么親人,于是便開口問道:“是有什么緊急的事嗎?待會兒我們吃完飯后去處理也可以。”
“沒什么,就是我買了秦始皇陵的門票我得提前趕到那里去參觀,票上說四點后不讓參觀了,聽說里面很大我得抓緊時間。”
“哈哈哈!原來如此,你大伯說得一點沒錯,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你和他的性子當真一模一樣,沒事的以后你天天看秦始皇兵馬傭,不需要今日這點時間走,叔帶你去吃好吃的。”
楊銘看了一眼揚志發,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著頭腦,但是他又不能拒絕眼前這個對他很好,第一次見面便把自己當親人的人,他只好跟著揚志發去吃飯了。
揚志發帶他去吃了西北特色菜,在飯桌上揚志發告訴他以后可以留到西安秦始皇陵工作,剛開始的內容就是每天打掃秦始皇兵馬俑,和清理場地做一些基礎的維護工作。
并且跟著揚志發的助手和他們一起做科研項目,楊銘聽見這么個好事后很是開心,原來他大伯的書信是給他介紹工作的并且還給他找了個落腳的地方。
楊銘來到西安一個星期后便在楊志發的安排下正式成為了秦始皇陵工作人員里面的一員,他做事很是認真,除了每天做些基礎的數據統計和簡單的清掃工作外,
他連安防工作也負責了,他總是最后一個離開,而且每次送給揚志發的報告也寫得很是精湛,揚志發有這么一個堪稱全才的助手也很是榮耀,時間如流水般,一晃大半年過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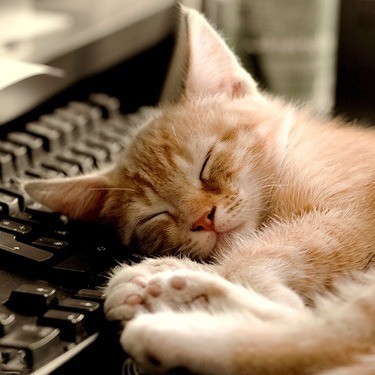
歸來者2
慢熱文短篇,若與某些名人重名純屬巧合。 本故事純屬虛構,不虛妄、不違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