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jié)束了下午的心理輔導(dǎo),我收拾東西準(zhǔn)備離開學(xué)校,發(fā)現(xiàn)一個男孩在門外悄悄地向里面張望。我微笑著向他招手,他見我發(fā)現(xiàn)了他,紅著臉走了進來。
這是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子,個不高,身材瘦弱,綠色的短袖T恤,牛仔褲,白色運動鞋,小平頭,戴著一副金絲黑框眼鏡。
“同學(xué),找我有事嗎?”我讓他在椅子上坐了下來,輕輕地問道。他沒有說話,眼睛緊緊地盯著自己的腳尖。我給他倒了杯水,他接過水,抬起頭看了我一眼,我笑了笑,在他對面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他把水放到了身邊的桌子上,雙手不停地揉搓著,“你是穆老師嗎?”我點了點頭,我在這所學(xué)校兼職心理輔導(dǎo)員,每周到校兩天,負(fù)責(zé)對學(xué)生進行心理疏導(dǎo)。他聽到我的回答,很小聲地說道:“穆老師,我殺人了……”
聽到他的話,我不由吃了一驚,但并沒有在臉上表露出來,我問道:“你殺了誰?”他說道:“我殺了班主任黎老師。”
黎老師是初二?三班的班主任,就在今天我還和她見過面。我長長地松了口氣,望著他淡淡地說道,“小同學(xué),說謊可不是好習(xí)慣。”男孩見我不相信他的話,情緒有些激動,“我沒有說謊,我真的殺了她,真的!”
他一邊說,一邊握住了我的手,“老師,我沒有說謊,沒有。”
我望著他的一雙眼睛,淡淡的憂郁里帶著迷惘,但卻不像是說謊的樣子。我問道:“你為什么要殺她?”他搖了搖頭,“我不知道。”我又問道:“你是怎么殺死她的?”這時我已經(jīng)有些懷疑,這個男孩的精神狀況出了問題,很自然地我便進入了心理醫(yī)生的角色。
他回答道:“我用一條毛巾勒死了她,剛開始她努力地掙扎著,掙扎著,突然就不動了!”他一邊說,一邊比畫著,最可怕的是他的目光中竟然透出濃濃的殺意。他的眼神讓我不禁打了一個冷戰(zhàn),正想問他叫什么名字,這時手機卻響了。
我輕輕地對男孩說道:“不好意思,我接個電話。”然后站起身來,走到了窗邊。
接完電話,回過頭來,男孩已經(jīng)不見了,我追出房門卻沒有發(fā)現(xiàn)他的蹤影。
收拾好東西,我沒有馬上離開,而是去了初中部的辦公室,我想找黎老師問問這個男孩的情況,我必須搞清楚這究竟是怎么回事。
“黎老師沒在辦公室,正在教室上課呢。”一個女老師說道。
在初二、三班的教室門口,我看到了正在上課的黎老師,她見我找她,便走了出來。我把事情大致地向她說了一下,她的眼中也充滿了疑惑,她說道:“我一直在上課,班上的學(xué)生都在,沒有人出去過!”
我伸頭向班里望了望,沒有看到剛才的那個男孩,我苦笑道:“或許是哪個頑皮的學(xué)生的惡作劇吧,黎老師,既然沒事我就不打擾了,再見!”
回去的路上我的腦海中總是浮現(xiàn)出這個男孩的樣子,特別是他的那雙眼睛。
第二天我才到心理診所便有警察找上門來了,他們告訴我黎老師昨天晚上被人勒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因為我昨天曾經(jīng)找過她,所以他們便找到我,想弄清楚我找黎老師做什么,我們都談了些什么。
我把事情的經(jīng)過向警察說了一遍,警察顯然不太相信我的話,他們看我的眼神中充滿了懷疑。負(fù)責(zé)這個案子的王警官問道:“穆老師,你說那個男孩告訴你他是黎老師的學(xué)生?”我點了點頭,王警官繼續(xù)道:“可我們在初二?三班并沒有看到你描述的這個男孩。”
我苦笑,“我昨天在黎老師的班上確實也沒有看到他。”王警官淡淡地笑著說:“穆老師,打擾了,如果你再看到這個男孩麻煩你盡快通知我們,這是我的名片。”我接過名片,把他們送出了門。
整個上午我沒有心思做事,讓助理冉冉把今天所有的預(yù)約都取消了,我決定再到學(xué)校去一趟,我一定要找到那個男孩。
“穆老師,你怎么來了?”高校長見到我有些驚訝,今天并不是我駐校輔導(dǎo)的日子。我對高校長說:“高校長,能不能和你談?wù)劊俊备咝iL點了點頭,“到我辦公室去吧。”進了辦公室,高校長給我倒了杯水,“你是為了黎老師的事情來的吧?”他看著我的眼神透著怪異。
我把昨天下午發(fā)生的事情又說了一遍,他聽完后問道:“這件事你告訴黎老師了嗎?”我回答道:“跟她說了,但她只是笑笑,當(dāng)時我們都以為是孩子的惡作劇。”高校長點點頭說,“如果你的話是真的,那么這件事情還真的有些不可思議。”他坐直了身體,“這樣吧,我叫人把全校學(xué)生的資料都送過來,你再仔細(xì)地看一下,有沒有你說的這個男孩。”
我很仔細(xì)地把全校一千多個學(xué)生資料翻閱了兩遍,沒有任何的發(fā)現(xiàn),我確定這個男孩一定不是學(xué)校的學(xué)生,可昨天下午的事情又如何解釋呢?
離開校長辦公室的時候,高校長叫住我,“這個案子警方已經(jīng)介入了,既然這個學(xué)生不是本校的人,那就交給警察去處理吧。”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讓我別再管這件事了。我點了點頭,回到了自己在學(xué)校的工作室。
關(guān)上門,我閉著眼睛想休息一下,理一理自己的思路。
“咚咚”。有人敲門,我過去把門打開,當(dāng)看清楚門口站著的人時,我愣住了,竟然是那個男孩,他的臉色蒼白,全無血色。
趁我發(fā)愣的時候,他走了進來,并且關(guān)上了門。
他徑直走到了昨天下午他坐過的那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我站在那里沒有動,我在想究竟要不要給王警官打電話,或者是通知校長。男孩扭頭望了我一眼說道:“穆老師,能陪我說說話嗎?”我忙說道:“哦,好的。”我決定還是暫時不告訴任何人,好奇心驅(qū)使我坐到了他的面前。
“我殺人了!”他輕輕地說道。望著他,我怎么也不相信,這樣一個文靜而瘦弱的男孩會是殺人兇手。我問道:“你為什么要殺黎老師?”他的臉上滿是痛苦的神色,“我不知道。”我又問道:“你叫什么名字?”
“炎陵。”他的聲音很小。
“穆老師,我不想殺人,可我卻管不住自己。”我拉住了他的一只手,“告訴我,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迅速地抽出了被我握住的手,詭異地看著我,“我說了,我不知道!”他站了起來,向門邊跑去,我一把拉住了他,他竟然張開嘴咬了我一口,我疼得松開了手,他跑了出去。
我追到了門口,和上次一樣,男孩早已沒了蹤影。
他叫炎陵,這是這次談話他唯一留給我的有用的線索。我跑到了校長室,高校長見我驚慌失措,問道:“怎么了?發(fā)生了什么事?”我喘著氣回答道:“那個男孩,他,他叫炎陵!”高校長皺著眉想了想說道:“我們學(xué)校從來就沒有一個叫炎陵的學(xué)生。”
是的,剛才我查閱了全部學(xué)生的資料,確實沒有一個叫炎陵的。
高校長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看你一定是沒休息好,回去好好睡一覺吧。”
我給王警官去了電話,把男孩的名字告訴了他,他說他會盡快調(diào)查,然后匆匆忙忙地掛掉了電話。我感覺王警官對這個案子并不是很上心,或者說,他們應(yīng)該也把我列為了嫌疑人,所以對我的態(tài)度并不熱情。
我悻悻地走出了學(xué)校,坐上公交車準(zhǔn)備回家。
“穆老師!”有人拍打我的肩膀,我扭頭一看,又是他!不知道為什么,自從聽到了黎老師的死訊后,見到這個男孩我就會感覺緊張。
“你怎么在這兒?”我問他。
炎陵回答道:“我的話還沒有說完,所以一直在學(xué)校門口等著。”我說道:“說吧,你到底還想說什么?”炎陵繼續(xù)道:“我殺了高校長……”正好公交車停了下來,沒等我反應(yīng)過來他便下了車。我跟著下了車,他的背影卻已經(jīng)消失在學(xué)校的方向。
其實我有很多話想問他,可是他卻沒有給我機會。
我突然想起,他說他殺了高校長,鑒于黎老師的事情,我有些擔(dān)心,于是掏出電話給王警官打了過去,王警官聽完我的話便問清楚我在什么地方之后,讓我回到學(xué)校去看看高校長有沒有出事。
我打了部車,重新回到了學(xué)校,飛快地跑到了校長辦公室。
高校長不滿地看了我一眼,“怎么又回來了?”我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道:“我怕你出事,所以就趕緊來了。”高校長不解地問:“我出事?我會出什么事?”我把男孩的話告訴了他,他陰沉著臉說道:“開什么玩笑,我不是好好地在這里嗎?”我知道高校長一定不相信我的話,他又問我:“那你有沒有問他,我是怎么死的?”
我愣住了,我確實忘了問,而男孩這次也沒有說。高校長冷冷地看著我,“如果沒什么事,請你出去,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沒時間招呼你。”我退出了他的辦公室,在走廊上點了支煙。
二十分鐘后王警官他們來到了學(xué)校,和高校長見過面后,王警官讓我和他一起到刑警隊去一趟,他的態(tài)度很強硬,仿佛我就是那個殺人的兇手。
上了車,我對王警官說:“警官,相信我,高校長有危險!”王警官身邊的一個小伙子看著我冷笑道:“只要你不在,高校長就不會有什么危險。”王警官瞪了他一眼,然后對我說:“你三番幾次說看到過這個男孩,可是你根本無法證明他的存在。”
是的,就連我自己都差點兒懷疑是不是真的見過這個男孩,可他又是很清晰地印在我的記憶里。
王警官繼續(xù)說道:“你昨天找黎老師到底有什么事?她是怎么死的?”我的情緒慢慢變得激動,“我說的都是實話,你們?yōu)槭裁床幌嘈盼遥俊蓖蹙僬f道:“你別激動,我們不會冤枉任何一個好人,當(dāng)然,也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壞人,我們并不是懷疑是你殺了黎老師,不過你有義務(wù)配合我們的調(diào)查。”
在刑警隊里,他們又反復(fù)地問了我那兩個問題,他們始終不相信我去找黎老師的原因,而我也提供不出有力的證據(jù)證明那個男孩子真的存在。
最后王警官把我送出了刑警隊,“穆老師,不好意思,我們這也是例行公事,你提供的那個名字我們也仔細(xì)地查了,全市一共有九個叫炎陵的,不過最小的年齡也有二十八歲。”我默默地點了點頭,王警官給我攔了部出租車,“回去好好休息吧,我看你今天的精神很差。”我從出租車上伸出手,拉住了他的衣袖,“王警官,高校長真的有危險。”他笑了笑,“我們會留意的。”
我回到家里已經(jīng)快八點了,泡了盒方便面,胡亂吃了兩口,便躺在沙發(fā)上。
我的腦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如何解釋這兩天發(fā)生的事情,那個男孩的影子總是在我的面前晃動,特別是他雙眼中的殺意,我一下子被嚇得坐了起來。高校長不知道怎么樣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時候睡著的,直到急促的敲門聲把我驚醒。
我看了看表,已經(jīng)是清晨四點多鐘了,站起身來打開了門,王警官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屋子里面,“你才回來?”我搖了搖頭:“早回來了,在沙發(fā)上睡著了。”他的那個年輕的同事問道:“誰能證明你一直都在家里?”聽到這話我心里一驚,“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年輕人說道:“你先回答我的問題。”
我想了想說道:“沒有人能夠證明,我一個人住。”年輕人沒有再說話,王警官坐到了沙發(fā)上,看了一眼我還沒來得及收拾的泡面盒子。我在他的對面坐了下來,“王警官,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王警官輕輕地說道:“高校長死了。”
雖然我的心里早已經(jīng)猜到了,可當(dāng)他說出來的時候我還是吃了一驚。我望著王警官說道:“我提醒過你們,高校長有危險,你們?yōu)槭裁床缓煤每粗俊蓖蹙僬f道:“我們一直跟著高校長,直到看到他和他愛人進了家才離開的。一個小時前,我們接到他愛人打來的電話,說他在家里的浴缸里溺水死了。”
我看了他的助手一眼,“所以你們又懷疑到了我的頭上,出完現(xiàn)場就往我這趕?”王警官尷尬地說:“穆老師,您誤會了,我相信你一定不會是兇手,但事發(fā)之前你曾經(jīng)說過高校長會遇到危險,我們只是循例來向你問問情況。”
我冷冷地說道:“我知道的情況下午已經(jīng)說過了。”王警官感覺到我的不滿,他笑了笑,“我想多了解一點關(guān)于那個男孩的事情。”我說道:“你們不是認(rèn)為他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人嗎?”王警官咬了咬嘴唇,“是的,我之前確實懷疑過是不是真的有這樣一個男孩,但今天晚上我在高校長的房間里看到一張他和學(xué)生的合影,很像你提到的那個男孩。”
說完他從身上摸出一張照片遞了過來。
接過照片,我認(rèn)真地看了起來,是他,站在高校長身邊的那個男孩子就是炎陵。我點了點頭,把照片還給王警官,“你沒有問高校長的愛人這個男孩的情況嗎?”王警官嘆了口氣,“我問了,可她說她從來沒有見過這張照片。”
王警官見我不說話,他站起身來,“打擾你半天了,我們也該走了,謝謝你的配合。”我把他們送出了門,“王警官,如果找到這個男孩能不能通知我一聲?我有幾個問題想問問他。”王警官點頭答應(yīng)了。
“穆老師,我們找到照片上那個男孩了。”王警官打來電話。我聽到這個消息很是激動,結(jié)束了上午的預(yù)約便打了一輛出租車向王警官給我的地址趕去。
這是城郊的一個智障兒童康復(fù)中心。
王警官迎了上來,和我打了個招呼,然后輕輕在我耳邊說道:“你確定照片上的男孩就是你見過的那個嗎?”我肯定地回答:“確定,怎么了?”他說道:“你先見了再說。”
王警官把我?guī)У搅艘粋€房間門口,努了努嘴,示意我和他一起進去。
我慢慢地走了進去,里面只有一張床,床上躺著一個人,那張臉我非常熟悉,就是我見過的那個孩子。我對王警官點了點頭,王警官沒有說話,靜靜地待在一旁。
我走到了男孩的面前,男孩仿佛沒有看到我一般,目光呆滯地望著遠(yuǎn)處。我輕輕地說道:“炎陵,你還認(rèn)識我嗎?”他緩緩地扭過頭來,看著我,并不回答。我回頭看了一眼王警官,他苦笑著搖了搖頭,“醫(yī)生說他有自閉癥,到這里六年了,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
我疑惑地說道:“可我們確實交談過。”王警官淡淡地回答:“醫(yī)生還說他根本就沒有離開過康復(fù)中心。”說罷緊緊地盯著我看,我能夠體會出他目光中的含義,在他的心里,從頭到尾我都在說謊。
我重新望向床上躺著的炎陵,是他,絕對不會錯,我伸出手去,想拉住男孩的手,男孩像是受了驚嚇一般,猛地把手縮了回去,用恐懼的眼神望著我。我輕輕說道:“炎陵,你真的不記得我了嗎?”他坐了起來,雙手抱著膝蓋,緊緊地抱著,那是一種防御,他是在防備著我。
一個穿著白大褂的男人走到我的面前,“你好,我是他的管床醫(yī)生。”我木然地握著他遞過來的手,他笑著說道:“你就是穆成老師吧?我看過你寫的幾篇關(guān)于催眠的論文,很受啟發(fā)。”我淡淡地笑了笑,“過獎了。”然后望著床上的炎陵問道:“你確定這幾天他都沒有離開過康復(fù)中心嗎?”他回答道:“我確定,還有中心的許多醫(yī)生和護士都可以確定,怎么了?”
我說道:“沒什么,謝謝了!”王警官走到我的身邊:“我們走吧。”我無力地點了點頭,跟在他的身后,離開康復(fù)中心。
上了車王警官輕輕說道:“你不想說點什么嗎?”我看了看他,“說什么?我已經(jīng)不知道能說什么了。”王警官發(fā)動了車子,“我相信你不會說謊,但這一切卻又是那么的荒唐,說給誰聽誰都不會相信。”我點了點頭,“你們是不是懷疑我?”
王警官笑道:“這不重要,就算懷疑,我們也拿不出證據(jù),現(xiàn)在重要的是盡快抓到兇手,對我們大家都有好處。”我問:“我能夠做什么?”王警官道:“你覺得這個男孩還會來找你嗎?”我回答道:“會,我覺得這個案子并沒有結(jié)束。”王警官聽了說道:“下次他如果再來找你,你一定要把他給拖住,然后想辦法發(fā)短信給我,我馬上就能趕到。”
三天過去了,每天下午我都會到學(xué)校去待上兩個小時,可那男孩再也沒有出現(xiàn)。
如果不是黎老師和高校長的死是事實,如果不是偶爾會接到王警官打來的電話,我會懷疑這一切是不是我的錯覺。
天漸漸地暗了下來,學(xué)生們已經(jīng)走完了,我收拾好東西準(zhǔn)備離開學(xué)校,就在這時,響起了敲門的聲音。我的心微微激動起來,也帶著一些恐懼。我輕輕地打開了門,外面站著的是王警官,我松了口氣說道:“你嚇?biāo)牢伊耍 ?p> 王警官見我緊張的樣子,輕笑道:“你以為是誰?”說完他反手關(guān)上了門。
我不知道他在這個時候來找我有什么事,他在沙發(fā)上坐了下來,“晚上有事嗎?”我搖了搖頭,他說道:“我?guī)闳ヒ粋€地方。”聽到他這話,我問道:“是不是有什么新的發(fā)現(xiàn)?”他笑笑,“去了你就知道了。”
“咚咚!”又有人敲門,王警官看了看我,我也看著他,他站了起來,“我先藏起來。”我點了點頭,等他在我的辦公桌下藏好了,我才把門打開。
炎陵就站在門外,門開了,他卻沒有想進來的意思。他的眼睛緊緊地盯著我,那目光很冰冷。我擠出一個微笑對他說道:“進來吧,有什么事情坐下慢慢說。”他沒有動,我伸手想拉他,他向后躲開了。
我想或許是王警官進來的時候被他看見了,所以他不愿意進來。
我望著他,輕輕地問道:“到底怎么了?”他還是不說話,轉(zhuǎn)身跑了。這時王警官早已悄悄地到了門邊,一把推開我,向炎陵追去。
幾分鐘后,王警官回來了,看樣子他并沒有追到炎陵。見到我,他搖了搖頭說:“這小子跑得太快,我沒追上。”我問道:“你也看到了吧?”他苦笑道:“看到了。”
我關(guān)上門,跟著他上了車。一路上我們都沒有說話,王警官不知道在想什么,而我卻在想炎陵找我的目的是什么,每一次和他見面都會有人死去,那這次呢?我點了支煙,王警官說道:“給我來一支。”我把剛點好的遞給了他,自己重新點上一支。
王警官吸了一口,然后說道:“你說這小子這次來會不會想向你傳遞什么信息?”他居然也想到了這一點,我回答道:“不知道,他一句話都沒有說。”我靠在椅背上閉上了眼睛,我又看到了那雙冰冷的眼睛,我突然有一種感覺,今天晚上還會有人出事,這只是我的直覺,我沒有說出來,因為我沒有任何的依據(jù),更不知道誰會成為下一個目標(biāo)。
車子開進了一個小區(qū)。我跟著他上了樓,他掏出鑰匙打開了門,然后在墻上摸索著,終于燈亮了。他在沙發(fā)上坐了下來:“知道這是哪里嗎?”我搖了搖頭,他輕輕說道:“這就是黎老師的公寓。”這確實是女人的屋子,暗粉色的色調(diào),還有著淡淡的幽香。
我也坐了下來,“你想讓我看什么?”他指了一下茶幾下面放著的一本影集說道:“你看了就明白了。”我拿起影集,慢慢地翻了起來。
大多是黎老師的生活照,黎老師雖然已經(jīng)過了四十,但從照片上看卻仍舊頗有風(fēng)韻。突然,我發(fā)現(xiàn)了一張合影,照片上一個女人抱著一個五六歲的孩子,女人是黎老師,而那男孩,看上去很像炎陵。
我慢慢地睜開了眼睛,發(fā)現(xiàn)自己躺在病床上,面前站著一個大約五十多歲穿著白大褂的男人,我驚訝地叫道:“董校長?”
“你醒了?”穿白大褂的男人微笑著看著我,我問道:“這是什么地方?”他回答道:“這里是琶洲總醫(yī)院,我姓炎,是你的主治醫(yī)生。”琶洲總醫(yī)院是一所精神病院,因為職業(yè)的原因,我沒少和這里打交道,沒想到現(xiàn)在我竟然成了這里的病人!
我的情緒開始激動起來,“我為什么會在這里?”炎醫(yī)生說道:“是兩個警官把你送來的,他們懷疑你有精神病,并且還有嚴(yán)重的暴力傾向,所以就把你送過來了。”我大聲地叫道:“我沒有精神病,我是個心理醫(yī)生!”
炎醫(yī)生冷笑道:“誰說心理醫(yī)生就不會有精神病了?你不僅有精神病,你還殺了人。”我突然想到了一些事情,我安靜了下來,輕輕地問道:“送我來的人是你兒子對嗎?”炎醫(yī)生先是一愣,然后笑了笑,“看來你病得不輕。”
我說道:“我想見見你兒子。”炎醫(yī)生說道:“你再也見不到他了,你的下半輩子,將會在這里度過。”說完他從身后拿出一份報紙,“好好看看吧!”
我接過報紙,一個醒目的標(biāo)題出現(xiàn)在我的眼前《心理醫(yī)生竟是精神病人,智勇神探巧破連環(huán)命案》。
文章中的我竟然成了一個有著嚴(yán)重癔癥的精神病人,殘忍地殺害了自己兼職心理輔導(dǎo)的學(xué)校的校長和老師,而最后查出我是兇手,并將我繩之以法的人便是英勇的刑警王吉安。
我冷冷地看著炎醫(yī)生,“我能問你幾個問題嗎?”他微笑著點了點頭,“問吧。”我問道:“整個事件的策劃者是你,對嗎?”他點了點頭,我又問道:“炎安在六歲走失的事情也是假的?”他又點了點頭。
我望著他說道:“能告訴我你們?yōu)槭裁匆獨⒗枥蠋熀透咝iL嗎?”炎醫(yī)生說道:“杜曉燕和姓葉的同流合污,還一直欺騙我的兒子。”說到這里,炎醫(yī)生的雙手抓緊了我床頭,“她能夠瞞住吉安,可騙不了我,你知道嗎?炎安和炎陵根本就不是吉安的孩子!他們只不過是利用吉安的地位和愧疚之心來滿足他們的一己私欲。”
看到他激動的神情,我的情緒慢慢地平靜了下來,“你既然早就知道,可為什么要等到現(xiàn)在才動手?”炎醫(yī)生說道:“姓葉的虧空公款,便利用吉安和杜曉燕的事情威脅吉安,要吉安幫他填補虧空。這樣的勒索,有一次就會有第二次,這樣的事情我絕對不能容忍!”
我望著這個憤怒的老人,“炎安和炎陵又是怎么回事?”他望著我,目光中露出猙獰道:“炎安是我炎人偷走的,我把他藏在了琶洲總醫(yī)院,沒多久,炎安便真正成了一個有著嚴(yán)重自閉與抑郁癥的精神病人,我是精神科的專家,做到這一點并不是難事。他們這樣對待我的兒子,我也要毀了他們的這兩個孩子。”
他頓了一下繼續(xù)說道:“接著我便找了個機會,把炎安與炎陵調(diào)了包,你要知道,在失去一個孩子之后,悲傷會讓他們失去理智的判斷,他們無法分辨出之后他們見到的炎陵已經(jīng)是炎安了,當(dāng)發(fā)現(xiàn)假炎陵患上了精神病,他們自然很快地就把他送到了我這里。”說到這里,晏老頭的情緒開始有些激動了,“可是我沒想到,這么些年來,我卻無法讓炎陵也變得和炎安一樣,你知道嗎?這對我這個精神科專家而言是莫大的恥辱。”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看來炎陵并沒有因為他的努力而患上精神病。
我問了一個我最關(guān)心的問題,“為什么會選擇我?”他嘆息道:“因為他們勒索我的兒子,我必須反擊,可這件事情總得有個人來頂罪,當(dāng)聽到你到學(xué)校做心理輔導(dǎo)的時候,我就知道機會來了,我便故意讓炎陵去接近你。”我問道:“你是說我見到的人是炎陵?他為什么會對我說自己是兇手?”
炎老頭說道:“雖然我不能夠讓炎陵和炎安一樣,但我卻能夠在他的心里種下仇恨,你想想,當(dāng)一個孩子知道自己的母親背叛了自己的父親,甚至伙同外人來對父親進行勒索的時候,他會怎么辦?”
這一下我完全明白了,我閉上了眼睛,搖了搖頭,沒有再說話,我知道這間窄小的屋子或許將成為埋葬我下半生的墳?zāi)埂?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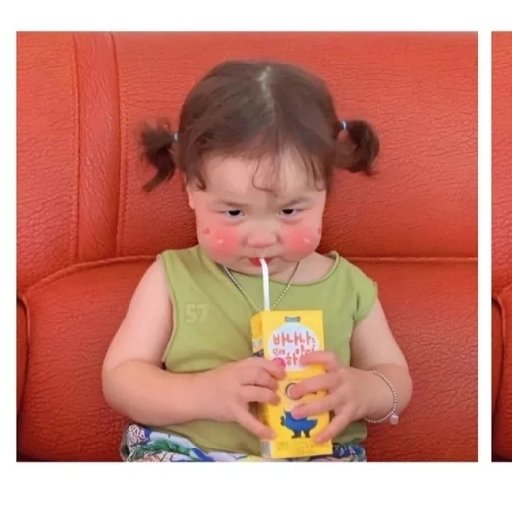
一念狂癡
吾日三更吾書,求推薦,求收藏,求月票,禮貌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