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承天見掌門大師兄心灰意懶,神情透著頹廢,已然無有昔日的豪氣大張,只因為他理想破滅,所以……傅傳書見袁師弟并未拿穴要了自己的性命,心下不禁茫然,想起當年自己幼小之時師父趙相承,其實他雖知師父既是爹爹,然則在他內心依舊不認為是這樣子,隱隱有種不可去除的隔閡,說不清道不明,也許只因師徒相稱日久的緣故,所以便有了生分。猶記那年隆冬數九寒天,忽地下起一場茫茫大雪,將昆侖派的玉虛宮、天壽宮、紅鸞宮、上清宮、九天玄女宮諸大宮殿掩映在大雪之中,一時之間整個昆侖玉指峰成了玉樹瓊枝的世界,仿佛蒼茫之間置身于云霄神仙之境。趙相承將傅傳書引到一座石室——那是絕少讓派中弟子親臨的地方,只見一盞渾暗油燈之下,正中供臺供奉著卻是一尊天尊乃是元始天尊又稱作玉清大帝,元始之意為道之祖炁,為世上天下萬物之始,天尊者為一靈至貴,天上地下唯此獨尊,至尊至極之意,其在道教之中是為開劫渡人,其居于玉清天神仙之境也!
其時趙相承低頭看這傅傳書眉清目秀之間又透著隱隱的俊逸之氣,直覺讓他覺得與自己有幾分相似,那時節他又哪里知道這傅傳書便是自己的孩兒?他讓傅傳書坐下,說起昆侖派歷代掌門的事情,多是反清復明之舉,然則說到自己這代掌門不由血脈僨張,言詞之間透著豪邁,不禁吟道:“雄哉權握天地機,上蒼不許自身奇!閑談王霸渾多事,鋒铓不露將誰知?憶昔余年十四五,明經早欲干明主。壯心不伏低時才,逐弄箋毫業詞賦!”當時傅傳書年少無知,然則對于反清復明的事情卻也知道,因為他時常下山隨師父采買藥物,見到伊犁城中的清兵對制下百姓蠻橫霸道,有時非打既罵,便想我也要做官做宰方不受人家欺侮,他卻不想“驅除韃虜,恢復中國”;也許要求一個垂髫小兒去做大人的理想似乎過為己甚,不切實際!
袁承天見大師兄神情乜乜呆呆,心想:掌門大師兄恕小師弟無禮了。他伸手將他拿到自己身前,大聲斥喝道:“現下王爺已死,你們的傅統領又且被拿下,還不投降更待何時?”他喝斥聲中尤見有些兵士在那多隆阿的鼓動之下有蠢蠢欲動之勢,似乎還要反擊!袁承天心想此時只有嚴陣以待,更要直斥其非,說明其中的利害關系:如要執迷不悟那么便是死路一條,但是若是放下兵器那么皇帝也過往不究,在大是大非面前要他們三思后行。多隆阿心想:你倒說得輕巧,我若依你所言棄下武器,那么皇帝非但不會饒我,反而認為是我慫恿多鐸王爺起了異心,想要篡奪天下,所以不可以放下手中兵器,既然事到如此,不妨一意孤行,反正橫豎是死,與其受人以柄,不如奮起抗爭或許還有機會。因為這多隆阿深諳皇帝為人,看似仁慈,實則心有城府,且又喜怒無常,又熟讀漢人策略,定然會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所以他認為袁承天以皇帝之名想要招降這十萬之眾,有些異想天開。他多隆阿可是久經陣仗,眼見王爺橫死,傅統領又為袁承天所拿,自己已然處于危境之中,然則說要他棄下手中兵器卻是不能,當此之時只有全力以赴,否則決難有幸理。
袁承天見這多隆阿不為自己的言語所動,知道他已有同歸于盡的想法,看來說話也是枉廢唇舌。多隆阿忽地連連冷笑,說道:“袁少俠在下有一點卻是不明白?”袁承天道:“盡管說來!”多隆阿又輕咳一下,說道:“你身為袁門少主,執掌著三十萬的門人弟子,可說勢力大熾;又且你們的袁門宗旨卻是“反清復明”,本來與這皇帝較量,——可是目下你卻幾次三番相助于他,豈不是與初衷背道而馳?”他的言下之意自是說這袁承天是非不分,和天下各大門派歸為朝廷無有區別,一樣是效忠朝廷;其實這有本質上的區別,因為那些江湖各大門派是為了自身利益而歸順朝廷,而袁承天之所以力阻這多鐸的行為,乃是為了天下蒼生,免其荼毒,不是為了個人得失,而是濟世為懷的理想,反而顯得知大義知得失知廉恥,而反觀他這位掌門大師兄反而顯得相形見拙,不堪大用!只是這說辭他又不愿義說給他聽,因為說給他,他也未必懂。多隆阿見這袁承天并不理會,心中怒火大熾,心想好小子你才多大,不過弱冠,此時便顯得忠義乾坤,肝膽昆侖了?
袁承天知道事不宜遲,他又申明自己的大義!多隆阿卻視如不見,置若罔聞,一揮牢便命眾兵士將其圍攏,此時已然顧不上傅傳書的生死了,自己保命才是緊要。傅傳書見他竟視自己如無物,自然氣惱異常,可是自己此時已然無有還手之力,因為袁承天對這位大師兄不放心,所以用重手法卸去了他的內功心法,讓他再也不可以再行胡亂殺人,形同兒戲!這其實是袁承天勸他為善的好意,可是在傅傳書看來卻是這位小師弟故意在人前賣弄武術,以示自己的武功,可見這位小師弟內功心法猶在自己之上,這真是奇哉怪也!因為當初趙相承可是在京城被困之時將本派的絕頂內功心法“三花聚頂.五氣朝元”的無上內功傳于自己,而小師弟則無緣,可是今日交手他的內功和這“三花聚頂,五氣朝元”的神功可說是一脈相承,似乎不分彼此,難道小師弟又得一位世外高人相授?可是這是不可能的事啊?因為昆侖派的這種絕頂內功心法只傳于本派繼承掌門衣缽之人,旁人只是無緣,所以這一點著實讓人想不通。——其實他哪里知道這位袁師弟機緣巧合之下在昆侖之巔,杜鵑樹下得遇本派師祖——林正眠——見袁承天資質人品俱是上上之選,且又見他正氣浩然,所以便以一生內功心法相傳,要知道昆侖派的內功俱是一脈相傳,所以袁承天自然而然之中便練就了這無上神功,甚而逾越原來的功法,這也是青出于藍而勝藍的原因所在!
多隆阿此時如此絕決自有他的道理,因為在他漢人是為夷邦之人,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也;對漢人和漢人將領尤為輕視,因為在他的固有認知中滿洲人才是上天之選,所以當年太宗皇帝橫掃八荒,一統六合,可說是天之驕子,奪取漢人的錦繡山河,是為有為之君,于是乎天聰、崇德年間崇尚武力,礪兵秣馬,可說為后來入關后第一位皇帝福臨鋪平了道路。
今日他見多鐸王爺橫死當場,傅傳書又為袁承天所挾持,自己如果依照這袁承天所說行事,雖表面看來似乎是上上之選,然則又有被皇帝處死的風險,畢竟他和多鐸王爺這一路南來多殺人命,反心已顯,既便皇帝格外開恩,只怕恭慈太后也不會放過——因為表面是少年皇帝親政,實則幕后是這位太后把控,只是不到萬不得已之時她是不會驟起發難,所以可以說皇帝有時還要聽從這位恭慈太后的懿旨,——因為他一向以孝道治國,從來不會違背太后的意思,所以看似皇帝掌權,實則是令出慈寧宮!又且這位恭慈從來都是心機頗坐,只要朝中有人貳心于皇帝她便暗中假手于人,讓四大顧命大臣上書皇帝于以嚴懲,從不故息,可見這位太后的厲害的手段;所以今日他決然不會授首于人,便是冒著殺頭危險也要將袁承天殺了,再將這一切罪責推托在這位傅統領身上,讓太后遷怒于他,可以一箭雙雕,既可殺了傅傳書,又可免去自己的罪責,這樣一來豈不是好?
袁承天見這多隆阿一幅死不臨改所樣子,心想看來自己只有全力以出,先要出奇不意拿下這多隆阿讓這些兵士忌憚自己武功,而不敢輕舉妄動,至于言正辰他們另當別策,眼下最為緊要的卻是如何讓這些洶洶的兵士穩定情緒,否則自己真的難以脫身了。
多隆阿可沒這好性子,手中揚刀讓眾兵士向袁承天廝殺過去。袁承天見他們如潮水般涌來,自顧不暇,只有舍下傅傳書揮手中軒轅神劍與前來的兵士廝殺在一起。傅傳書倒地也無人顧他,卻也無人踩他,因為畢竟他是統領大人。多隆阿見袁承天向西北退去,只留下了地上的傅傳書,見他眼神之中再無昔日崢嶸,反而愈加顯得迷茫,也許是他大夢成空所致吧?
袁承天只所以邊戰邊戰,自有他的考慮,因為這正是讓這多隆阿以為自己勢不敵眾只有邊戰邊退,讓他掉以輕心,然后自己再出奇不意沖殺過來將他拿下,不把他們這些兵士不就范。這多隆阿那里會猜中袁承天心中的計較,還以為是他適才幾番出手,武功內力不逮所致,所以便要讓幾名兵士將這傅傳書抬回軍營再做計較,因為袁承天點穴手法高深,讓這多隆阿也是無從下手,只有緩圖他策!
袁承天見這多隆阿欲偕眾兵士回軍營,心想時機來也!他手中軒轅神劍忽地一招“劍指天南”迫開眾兵士,看似尋尋常常的一式劍招,卻是蘊含無上真力,氣息到處竟將周遭之人轟然掀翻在地,可見他已是全力施為;然后以腳撐地,身形高高躍起,于空中又是幾招換式變位,接著“鶴唳九重天”以昆侖派的無上的輕功,躍過眾人頭頂,轉身變位落在這正在前往軍營的多隆阿前頭。這下突起之變,任誰都未想到袁承天擊戰多時,竟然內息不減反見增強,便是這輕身功夫都是余人所不及。其實他們哪里知道這昆侖派的“三花聚頂.五氣朝元”的內功心法講究的是遇弱不弱,遇強則強的道理,所久袁承天雖
久戰而內功心法并不減退,反而有愈戰愈勇的架勢。這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這也是昆侖派的內功心法異于別派的原因所在。
袁承天這一套輕功動作行云流水,可說是一氣呵成,絲毫不拖泥帶水,直讓眾人看的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袁承天身子著地,旋既出手二指并攏點這多隆阿將軍的身上幾處大穴,讓他立時不能動彈。本來多隆阿一生征戰,身經戰場,臨敵經驗自當多變,不至于一下便被袁承天拿捏,其實這一切皆是他疏于防范大意所致,無關乎武功一道。待得眾人反應過來,這位多隆阿已然不可動彈。袁承天低聲喝道:“你們為何還執迷不悟,難道還要抗旨不遵,要知道忤逆追反可是殺頭重罪,有時還會禍及家人,你們縱然不怕死,難道爹娘也棄之不顧么?”
他這番話出自肺腑,所以有些持刀而來的兵士便止住了腳步,心中在想:可不是,為了別人的野心,我們干么要拼上性命?這樣卻然不值得。有時軍營之中最怕軍心渙心,所以只要有一人幡然醒悟,便會有身后無數的人響應。多隆阿見這些兵士舉起的刀槍又緩緩放下,知道他們皆為袁承天言語盅惑,看來真是大夢成空了,不由心中傷感連連,英雄末路!
袁承天見他眼中落下兩行濁淚,心想:若知今日何必當初?也許人生從來沒有后悔二字?因為路是自己走的,須怪別人不得,縱然前面荊蒺和陷阱也要去闖,再無后退可言,因為人生豈不就是充滿了無盡的挑戰和磨難?
袁承天見自己的話起了作用,又道:“當今少年皇帝心胸寬廣,仁義待人!我此次前來之時便全權相授,要我便宜行事,所以今日只要你們棄戈悔過,便于既往不咎,赦其死罪,所以今日我帶這多隆阿將軍和傅統領且去面見皇帝,俟后便來處理軍務。”
他話音剛落忽然有個陰惻惻地聲音傳來,“且住,袁少俠你這便要走,是非太自以為然了,全然不把我等放在眼中?”袁承天抬頭一張,只見僵尸門掌門言正辰正悠悠轉來,看似不疾不徐,可是轉眼之間便已到了眾人眼前,那刺人耳膜的聲音卻仿佛揮之不去。接著身后便是武當派掌門趙天橫、滄浪門管云濤、黃山派掌門杜永名三人齊齊現身,只是那不嗔和尚適才不敵袁承天一氣之下跺腳而去,表面服輸,實則心中怨悔叢生,以為今次自己大大地丟了臉色,無顏再效力于王爺,所以便揚長而去。
適才這幾位江湖人物之所以作壁上觀,其實都是出自私心,希望他們自相殘殺好漁人得利,不管誰生誰死于他們都是無害,只是有一點是他們幾人始料末及,便是袁承天竟可以憑一己之能讓這些眾兵士放下武器不做反抗,這是他們所未想到的。他們之所以并不遁去,而是要攔下袁承天也是出自私心,想要趁火打劫出手殺了袁承天,那么袁門勢必群龍無首,便可各各擊破,自己的門派可以在江湖聲名鵲起,不然今日由他自去,便是虎入歸山,龍游大海,以后想要聯手制衡袁門只怕也難,所以幾個人一合計不如攔下他,讓其乖乖就范!只是他們幾人將事情想的焉也簡單,如果袁承天輕易就范,那么他也便不是袁承天,也不配做這袁門少主了!
只是有時為了名利得失,有人便容易利令智昏,做出不智的事來,便如趙天橫他們幾個人,以為此時袁承天久經戰斗,已是力有未逮,強弩之末,便可以以逸待勞,一戰決勝負,好張大自己門派的聲名,只是有一點他們全然忘卻了——這袁承天可是身有昆侖派的無上的內功心法,自然非同小可,更兼有軒轅神劍相助——這軒轅神劍本是不世出的神兵利器,乃是漢人之祖軒轅皇帝所持有,當初殺妖除魔,世人莫其敢擋,又且秉承天地之間的一股正氣,是為世上真正的英雄所配有,余人皆是不堪。想這袁承天乃是袁督師后人,秉承先人之驅除韃虜,恢復中國之理想,是個英雄,其行為氣慨有遠邁前代英雄的氣勢,所以更可以說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他的行為武功自然不同凡響,否則亦無能一人領袖袁門這三十萬之眾的弟子?只是這其中利害關系這幾位江湖門派掌門全然未想到,只是盤算如何殺卻這袁承天,好漁人得利!
袁承天以目視之,但見這言正辰、趙天橫、管云濤和杜永名諸人都是虎視眈眈,一幅枕戈待旦的樣子,非但心中不懼,反而覺得心中好笑,心想你們想要殺我,只怕也沒這么容易。他本來倒提的軒轅神劍又自回于右掌之中,輕輕捏個劍訣,一記武林中最為尋常的招式“分光尋龍”,只覺隱隱之中便有一股攝人的寒光一閃而過,自有一種懾人膽寒的氣勢,便是那趙天橫他們幾人見狀也是不由自主地后退,似乎懼怕這袁承天忽起發難!其實說到他們幾人悍不畏死,也不盡然,世上又有幾人如當年袁督師一般肝膽昆侖,義氣千秋,只為了大明的萬里錦繡山河不受韃虜侵犯,然則他終于無力回天,只有忍看山河淪陷,置天下千千萬萬的無辜百姓流亡于道路!
待得趙天橫諸人見袁承天出此劍訣無意出招傷人之時,神情之中透著尷尬,心忖:我們幾人可都是英名遠播的名門正派的掌門,怎么今日反而忽生膽怯,害怕他一個少年不成?若然這消息為外人得知豈不是英名盡毀,貽笑大方?不成,我可要找回場子,不能讓這袁承天得意忘形,不知天高地厚!
袁承天盡將他們這些行動看在眼中,心中但覺好笑,心想他們這些自命俠義中人,說到底也不過是沽名釣譽之徒,那有什么民族至上,家國情懷?趙天橫是他們幾人之中性情最為暴躁的人,眼中揉不得沙子,更加不能見到別人輕視自己——因為他可堂堂派掌門,豈能由他人小視。他見袁承天看他們這干眾人神情之中透著鄙視,心想:好小子,你年紀輕輕也不過弱冠,便枉自托大,沒了江湖禮數,視我等前輩高人如無物,真是可惡,今日我等若然拿不下你,那才叫可笑?他唰地一聲響聲,已然拔劍相向。這動作竟快的出乎眾人意料!
趙天橫雖身為武當一派掌門,然而卻功名心重,總是舍不下世間的榮華富貴,與道家清靜無為的信條可說是背道而馳。因為在他看來和朝廷做對,無異于以卵擊石,自尋死路,所以便投身多鐸王爺,希翼他君臨天下,可是偏偏卻橫死軍營,似為袁承天所害,本來可以馬踏張家口,但是有袁承天強自出頭,橫生變故,所以只怕都成一夢!眾人自然將這無名惱怒遷怒于袁承天,再有便是當今之世也只有袁門在與朝廷周旋,其它門派都歸為朝廷節制,所以這袁門聲威在江湖之中日隆,顯得不與濁世同流,凸顯自己清高,讓他們這些自詡名門正派的人情何以堪,所以袁門成了眾矢之地,似乎不合乎當今,處處與眾不同。
趙天橫思之再三只有解決了袁承天,那么袁門勢必群龍無首,便可以助朝廷各個擊破。他還在枉想拿下這袁承天,只是他這想法未免兒戲。袁承天見本來可以說降這些叛軍,讓他們人人悔過自新,可是趙天橫他們卻橫加阻攔,非要與皇帝一爭長短,可是真是自不量力,不知天高地厚,想這紫微星座豈那么容易被旁人奪去?只是這道理雖然人人心里明白,可是還要逆天行事,因為每個人心中都有心魔,所謂心魔一起,禍及無辜;心魔已滅,萬事無憂!可惜不是每個人都能控制自己的心魔!所以趙天橫一幅兇神惡煞的模樣,似乎瞧誰都不順眼,尤其對袁承天更是恨之入骨;因為有他袁門,他武當派便顯得平平無奇,毫無建樹,似乎隨波逐流;而袁門卻彰顯世間大義,更加肝膽昆侖,忠義乾坤,——本來袁門便是秉承當年袁督師的遺志: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其行為可說是名正言順,不是矯情,而是袁門弟子人人情出肺腑,所以世人但凡說起袁門便情不自禁豎起大拇指說一聲:好氣派,好英雄;而對于其它江湖中那些所謂的名門正派便自呵呵冷笑,笑而不語,其意不言自明。世人還是分得清好與壞,誰是英雄!
言正辰、管云濤和杜永名見這武當掌門欲對這袁承天除之后快,一勞永逸,心想憑這趙掌門似乎難以對其構成威脅,莫若我等也加入,這樣一來似乎十拿九穩。他們三人以目視之,便已然心意相通,便向趙天橫走來。趙天橫又是何等樣人,自然心領神會,心想這樣也好,因為自己武當派武功雖然成名甚久,然而面前的袁承天雖年紀甚輕,然則卻有非同尋常的武功,自忖也沒有十足的把握,所以多一個幫手便多一份力,未嘗不是好事。他并不加以反對,反而以頜示之。
言正辰幾人見趙掌門并不反對,心想今日合我四人一力未始不會成功,所以都氣勢倍增,向袁承天圍攏而來。袁承天見他們要合圍自己,也是公然不拒,將軒轅神劍又從背后掣出,心想:今日且看誰是英雄?誰又是卑鄙無恥小人?趙天橫呼哨一聲已是出劍向袁承天小腹刺去,竟不謙讓,有失大家風范。余眾言正辰也掣喪門棍在手聯合杜永名和管云濤一并殺去。但見寒光颯颯之中四個人都顯得冷酷無情,一心都要將之殺之而們快。袁承天見了此情此狀心想我憐世人,奈何世人害我!原來天下最惡的不是禽獸而是世上的人心;正所謂人心叵測,如鬼如魅,只是無處遁形,終有顯形的一日,便如今日這幾位江湖名宿平日聲名赫赫,似乎是以自身衛護江湖正義,實則卻是為一己之私可以出賣良知的人,有時還不如鄉下尋常之人,因為他們還知道世上之事有可為,有可不為,還知道民族大義,自己的本來面目,所以有時仗義每多屠狗者,負心多是讀書人!
惡風不善,四人四種不同兵器襲來。只見趙天橫手執一把青鋼劍,看似尋常,實則是武當派歷代掌門的執掌信物——玄武劍,故老相傳為玄武大帝當初誅魔殺妖之時所用的神兵利刃,然則與袁承天的軒轅神劍似乎又有不足,略有遜色,不能相提并論。世間之神兵利器,仁者居之光明正大,所謂從善如流,便是濟世安民;而奸邪之人得之,便是為禍天下,生民涂炭,自此而后哀哀于道路不絕也!其后是言正辰手提喪門棍揮舞而至、黃山派的杜永名則是一柄魚鱗刀,寒光閃閃、管云濤則是一根竹桿——其實是精鋼所鑄,只是漆了綠色,所以不知底細的人還以為是尋常竹桿,不免大意,無形之中便疏于防范,實則這竹桿中空,內有機關,只要扣動機關,里面便會射出細如發絲的毒針,針上淬有本派的獨門毒藥,可說見血封喉,只要射中敵人再無生還之能,只要尋常這管云濤并不使用,非到萬不得己他才使用,往往趁人不備,以出其不意的手段射殺敵人于無形之中,只因他少有使用,所以江湖中極少有人知道,今日他見這袁承天神威凜凜,仿佛天神一般,無所畏懼!他們四人如果不全力以出只怕猶難勝他,所以他便暗暗下了注意要以這非常手段,否則如果他們四人不能夠勝他傳場出去,以后在江湖中如何立足,所以非要以非常手段不可,這也講不得什么江湖規矩了。
趙天橫從來自詡是名門正派的掌門,自認為自己是執掌道教之牛耳;所以今次便首當其沖,仗劍殺來氣勢洶洶,仿佛不可一世,似乎性命不要也要將之斃于劍下。袁承天雖則群敵環伺,然而心下不怯,因為他知道自己背負著家國使命,不是一個人的行為,假使今日囿于人手,那么袁門又算什么?這袁門三十萬之眾的弟子又該如何自處,所以他心中不由心脈賁張,豪氣縱生,心想古來俠義之士,多是慷慨悲歌之人,想那郭解、朱家之流為人排難解紛,那里斤斤計較;自己今日但教有三寸氣在,決然不會退卻,想古往今來的仁人義士多不畏死,何況自己!正是:藉交唯有不貲恩,漢法歸成棄市論。平日五陵多仁俠,可能推刃報王孫!(世傳郭解之人其貌不揚,而且性情暴戾,少時私鑄金錢,盜人墳墓,屢犯人事,年長之后稍有轉變,以恩報怨,廣施援手。后來為他憑公正處理外甥之死,又且寬容傲慢者,調解洛陽糾紛而名噪一時,備受世人尊崇。元朔二年,家貧的郭解因官吏忌憚而被遷茂陵,由此和楊家結仇,流亡期間,他憤起殺了楊季主,朝廷有司布告天下,緝拿于他,于是乎只有四處逃竄,后來籍少公為助其出關而慷慨自殺斷了線索。后來儒生詆毀郭解被門客殺,公孫弘定其大逆不道,于是家族遭誅,誠然一大悲哀!)
袁承天于刀光劍影之中執軒轅神劍游刃有余,并不著慌,因為他已然心中不驚,也就不加畏懼,只是全力以出,倒要看看他們的真實本領。軒轅神劍一出,鬼神皆驚,而且世間的凡兵利器皆要退避,無可與之爭鋒;只是他們這四人手中的兵器也決非凡兵利器,所以一時倒難分伯仲。趙天橫見這袁承天迎戰他們四人尤不落下風,而且招式老道,處處顯得大家風范,絲毫沒有怯場,不由讓人刮目相看;因為先前他還私下袁承天之所以可以領袖袁門,只不過是倚仗其是袁督師后人的名頭,未必有真實本領,所以對他這袁門少主很不以為是,以為是徒有虛名未必有其實,所以心中生了輕視,至于他手上的軒轅神劍雖然是神兵利器,然則他未必可以得心應手,所以都不怎么在意,可是現在看情形卻然不是,只見他將《國殤劍法》使將出來,只覺落葉秋風且又殺氣直懾人心脾,又覺天地之間忽然陰氣蒼茫,不知何時青天白日起了霧氣,將人罩身其間,看不清彼此,似乎此時只要袁承天暗中忽襲便可以任出一劍刺殺一人于當場,只是他不愿以這卑劣手段殺人,那誠然不是英雄好漢所為,污了袁門的名頭。
他忽然運氣丹田,氣發喉頭,忽作仰天長嘯,壯懷激烈,聲如龍吟虎嘯,竟而蕩盡妖氛。而后他有感而發吟誦道:“北客翩然,壯心偏感,年華將暮。念伊蒿舊隱,南柯夢,遽如許……回首妖氛未掃,問人間,英雄何處……”一時間念及過往之事,國破家亡,淪陷于夷狄,而天下幫派卻是認人唯親,人人反認他鄉為故鄉,忘卻了自己的本來面目,可不生悲?其實詞中所謂北客翩然,壯心偏感,年華將暮卻是心有同感——只是他還是少年,卻未年華將暮,然則這些年久經憂患,亦知生之不易死又艱難,回看自己一人獨支,天下人皆認為自己不通時務,枉想逆天改命,可不是愚不可及?可是誰又知道他從來都是秉承袁門抑或先祖袁督師的忠義千秋的信念,至于生死則置之度外,因為他知道天下事有可為有可不為!所以他仿佛孤懸于眾星之外,流浪無著的天煞孤星——雖然一生孤苦,處處受人排斥和冷落,然則卻有一顆排難解紛的豪情壯志,雖然久歷憂患,忍看周遭至親之人一個個離世而去,覺得此生不過大夢一場,何求何得?有時他也想放棄,也想青山藏我身,可是每每見到天下哀哀于道路的民眾,便放棄了成見,還要砥礪前行,因為上天有顆啟明星引導他前行,仿佛中有聲音:承天你不可以放棄,因為天授于命于你,你怎么可以一蹶不振,哪里有袁門后人的的風范?且問死且不懼,何懼世間憂患?他亦知如果自己一味沉淪毫無作為,那么哪世的爹娘也要斥責他為不肖子孫,因為漢人雖也懦弱,終要復國!
他的這一長嘯聲中,陰陰沉沉霧氣一掃而光,似乎為其胸中浩然正氣所攝,頓時遁去無蹤。趙天橫實在未想到他一喝之中的底氣如斯威力,由此可見昆侖派的內功心法確有獨到之處,非別派可為,不由得收起了小覷之心,心想:若今日我等不能勝了這姓袁的小子那才教可悲。他想到此處便又揮劍而上,招招不離他周身致命要穴。言正辰也相機行事,手中喪門棒舞得風發,擊向袁承天頭頂百會穴;管云濤掌中竹棒迎風一擺,暗下死手斜刺里向袁承天下脅刺去;杜永名一柄魚鱗刀迎面斫來透著無盡的狠毒,似乎與這袁承天有不世之仇。
袁承天見他們人人面露煞氣,哪里有名門正派一派掌門的風范,心想天下盡有沽名釣譽之徒,徒有其名,真是讓人可笑!記得書上說“盜亦有道”的話,先前不信,以為世上的盜賊和響馬那有為善之人,可是行走江湖之間才明白果不其然,有時草莽盜賊勝于廟堂之上那些侃侃而談的正人君子,不禁讓人感嘆天下人心最惡,人心難猜,自古皆然。漢時一代英雄漢陰侯韓信一世英勇,不想竟死于婦人之手,由此可見英雄末路都是悲哀,似乎無可逃脫。
袁承天見他們刀來劍往,便運劍如風,再展那《國殤劍法》中的“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鬼魂魄兮為鬼雄”這四招國歾劍法,四招之中蘊含天地同悲而英雄不死的氣概,直追千古,后無來者,劍招奇崛,每每出人意外,讓人避之不及,躲之不閃,可說這劍法曠古未有,加之有軒轅神劍更是威力倍增,世出無右!
趙天橫他們四人被這四招劍式回擊,幾乎都拿捏不住手中的兵刃,幾乎脫手而飛,還好他們有深厚的內功,否則非當場出乖露丑不可。人人都倒吸口冷氣,打起十二分精神,不敢有絲毫大意。袁承天本無意傷人,只是這四個人仗著前輩高人的名頭自以為是,非要難為于他,所以他不得不出手教他們以為怎樣作人,莫要頤指氣使,盛氣凌人的樣子。所以他并不手下容情,心想對惡人只有以惡制惡,決不故息,否則人家非但不感激人還以為你懦弱可欺!天下事從來如此,也不是新近才改變的,所以他劍之所到,都是鋒芒畢露,無形的劍氣之中透著咄咄逼人之勢。
趙天橫見狀氣得無以復加,他身為一派掌門幾曾被一個后生小子如此戲弄于掌上,這是從來未有之事,可是真是豈有此理?所以他滿肚子都惱怒,雖然手上劍招加快,想要一劍刺穿這個姓袁的少年,然則卻不能如意,劍劍落空,竟然傷他分毫不得,你說這可不是氣人之極。言正辰、管云濤和杜永名雖有心卻無力,因為他們武功遜于這趙天橫,所以便力有未逮,只是并不氣惱,心想:你堂堂武當掌門都不能勝這小子,又況且我等?所以他們一時倒不聒噪,反而心平氣和,似乎要看這位趙大掌門如何扭轉頹勢。趙天橫豈又看不出,心中哼了一下“好小子你們也看趙某的笑話?”這正是:文人相輕,武人相重;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從古及今皆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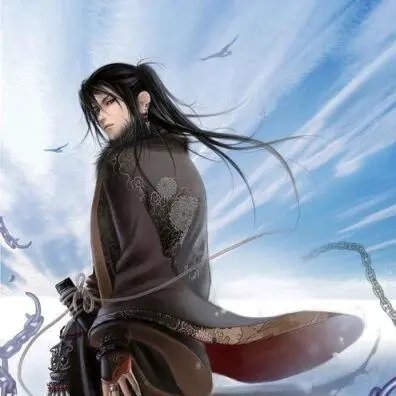
劍南生
文中袁承天所吟誦問英雄何處,再掃妖氛出自宋人朱敦儒《水龍吟》詞牌!其全詞是:放船千里凌波去,略為吳山留顧。云屯水府,濤隨神女,九江東注。北客翩然,壯心偏感,年華將暮。念伊蒿舊隱,巢由故友,南柯夢,遽如許。回首妖氛未掃,問人間,英雄何處。奇謀報國,可憐無用,塵昏白羽。鐵鎖橫江,錦帆沖浪,孫郎良苦。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有淚如傾!詞中道盡英雄不遇真主,苦讓夷人踏我河山,空有報國之志,奈何無以付人之感慨,所以有淚如傾,道不盡千古悲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