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育,我想見一個人。”
她一臉祈求的看著我,她明知道我最受不住她這樣,我只能幫她。
“她是我學校里的一個女孩。”吳憶試探著開口,就像是怕別人聽到一樣,“她之前和我表白過,我想我該給她一個答復。”
她說出這句話我并不意外,之前我了解到即使并不是特別美,但追她的其實很多,得到的原因也很統(tǒng)一,比如耐看,或者有氛圍感。
“她在哪。”
“現(xiàn)在是回家周,她應該在家,你可以幫我去找她嗎。”
吳憶的眼睛很好看,是棕色的,里面泛著綠感,就像是琉璃,我經(jīng)不住她這樣看我。
她給了我一個地址,我?guī)е钠诖瞄_了門。
“你找誰。”
開門的是一個男生,初中的樣子,我脫口而出耿歌二字,男生側(cè)身讓我進屋等會,自己走進臥室將人叫了出來。
“你好,你找我嗎。”
我瞥向男生,不知道他們什么關系,“抱歉方便借一步說話嗎。”
“沒事的,就這說吧。”
耿歌并沒有當一回事,我便沒再糾結(jié),抬眸盯著相對而坐的她,“吳憶認識吧。”
她聽到名字后我注意到其喝茶的手顫了一下,隧雙手撐腿,“她怎么了。”
“她想見你一面。”
我將人帶到病房就離開了,我不知道她們具體說了什么,我只看到耿歌是哭著走的,屋內(nèi)吳憶也垂頭喪氣。
她說身體好累,費用也好貴,不想再撐下去了。但是她把手機遞過來的時候我看到的卻是一群人勸她好好生活。
我不知道她們有沒有了解過胃癌,我只知道她活不久了,無藥可醫(yī)。
她緊攥著我的手,帶著哭腔的和我訴說,說他們滿嘴跑火車,吳憶說她也想好好生活,可是這個病治不了。
“程育,正義的光在我身上晃了一下,你懂嗎。”
“什么...”我當時并不太懂她說的是什么意思。
鐘表走到數(shù)字五,外面拼命鉆進來的風好像在催著我回家,取下衣架上的風衣。
三月初的春天很暖和,樹枝剛冒綠芽,一切生物都重獲新生的樣子。
可是我不喜歡春天。
在冬季,白雪茫茫千里冰封的感覺會讓我舒適,我一向怕冷,可對于冬季,我沒有任何理由拒絕。
到家吃過飯我便睡了,因為有些乏,一直睡到了中午11點多,隨手抓了個面包墊了肚子就想著去找吳憶給她解悶。
很奇怪,一路上很多人都在竊竊私語,緩緩推開病房門,可是我只看到空無一人的房間,我慌了。
順著人流奔向天臺,我一路踉蹌的擠到最前面。
她穿著單薄的病號服,背對樓外面向我們,身子后仰,雙手支在兩側(cè)。
吳憶那琉璃一樣的雙眸看向我,我上前一步卻又頓足,我想我沒有立場阻止她。
人是冷漠的。
樓內(nèi)是同病相憐的人,她們都想活著,可是這是老天的不公。樓外在下面看熱鬧的人,不嫌事大的叫囂快跳。
眉毛一直緊鎖不敢放松,我也怕她跳,但我沒有立場勸她。紅唇微啟,眼眸里充滿對自由的渴望,“程育,看看我的郵箱。”
“那是我新改的。”
“看到名字后,你會懂的。”
她今天的妝很好看,特別美。
隨著話語落下,她敞開雙手向后倒入,在人們的驚呼中摔了下去。
阿姨來的很遲,只看到她摔得殘破不堪的樣子,我將弟弟攔住,雙手覆上他的雙眼。
“吳慮,姐姐她自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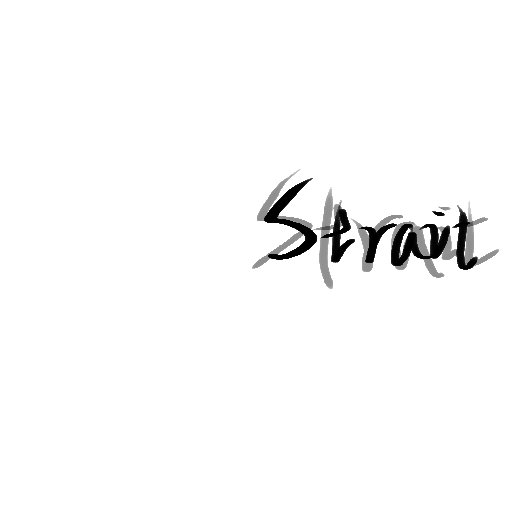
計算機囚徒
結(jié)尾了包包們,我開始碼她們的自述了哈。
